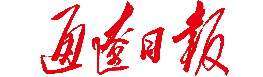□李富
2017年的正月初一,我们大包小裹装了一后备箱礼物,一家三口驱车前往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县见一个特别的人。我们的心情说不上是高兴,也说不上是忐忑,应该是很急迫。这个人及这个人的儿女,我们彼此都没见过面。这个人名叫李淑芝,当年八十九岁,是我的亲大姑。
一
我父亲1937年出生在河北省青龙县官场乡北稍峪村。这是一个群山环绕的小村,我的爷爷守着一点儿薄田过活,没有什么手艺,孩子又多。不要说当时中国大地被异族侵略,民不聊生,就是那几分薄田也养活不了家人。七分山,二分水,一分田。一个棉袄大的地方就是一块田。这次河北之行才真正理解了父亲常说的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一眼望去全是陡峭的石山,磨盘大、院子大的土地都被平整出来种上了庄稼。当时,爷爷有四儿两女,父亲上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大姑李淑芝七八岁时就被卖到邻村贾杖子贾家做了童养媳。父亲七岁的时候,爷爷决定跟族人迁徙到有土地耕种的地方,把儿女带出大山。两挂大胶车拉了满满几户人家几十口人和生活必备的一点点家当。车路过贾杖子村,大姑哭喊着跟了几里路,可是车上挤满了人,再也容不下一个瘦弱的孩子,大姑那年才十五岁。从此她和这个家族失联了近一个世纪。我和爱人坐在炕头上,一人握着一只大姑的手,听大姑讲她那悲凄的故事,陪她一起流泪。“我要是上了车,你奶奶就得下来,那家子人没有你奶奶可怎么活呢。”大姑最终原谅了遗弃自己的父母。
二
大姑做童养媳的贾家应该有几个钱,雇着长工。大姑上无公婆,丈夫参加了东北抗日游击队,大姑称“八路军”,他长年在外,大姑和贾氏的哥嫂过活,其实大姑是贾氏兄嫂买去的奴隶。大姑洗衣、做饭、喂猪,承包了所有的家务,还要上山砍柴。小小的年纪,瘦弱的身体却承担了成人的劳动。她做出饭自己也不能吃,嫂子让她单独熬粥,熬粥省粮食。有一次,她的嫂子打算将吃剩的米饭喂狗,转而改变主意施舍给了大姑,说:“给她点儿吃吧,长点儿力气好干活。”最让大姑气愤的是,嫂子盗走了大姑藏在棉袄里的十块大洋,这是爷爷留给大姑活命的大洋,是爷爷卖掉了大姑的自由换来的大洋……贾氏兄嫂偷了大姑的钱去县城下了好多次馆子。本是同样愚弱的一群人,在欺凌弱小的时候却是毫无人性。有一次,大姑得了痢疾,四五个月汤米不存,人瘦得皮包骨,家里的长工和村里的好心人实在看不下去了,给了大姑一些草药,告诉她:这些草药能治拉肚子,只是你的身体太弱了,一定要少吃。大姑每天吃一些草药,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三
等大姑有了孩子,姑父就和兄嫂分家单过了,大姑也从此摆脱了兄嫂的虐待。可是好景不长,姑父在从部队回乡休养的途中被人杀害了,是皮鞭毒打致死。杀害他的是伪满政府的治安队,也就是替日本人做事的“二狗子”。有人把姑父被杀的消息告诉了大姑,大姑背上不满周岁的女儿去找姑夫的组织,遇到盘查的,大姑就说家里没粮了,要到下面村子亲戚家借点米。大姑找到了区小队,区小队袭击了伪保治安队,活捉了六个杀害姑父的治安员,并捆绑了交由大姑处置。大姑说:“这六人中还有一个女的,他们各个给我磕头做揖,有的还说给我五亩好田,只要让他们活命。谁要你的田?你们把我的男人害死,让我们孤儿寡母失去了依靠!”大姑对游击队长说,她只有一个要求,要那六人脱光上衣,给她一把烧红的烙铁。大姑用烙铁烙了六个“二狗子”的后背,出溜一烙铁问一句:“你还害人不!”大姑的仇恨上升不到家国仇、民族恨。她的这几烙铁完全是身世之苦、亲人离弃之痛、丈夫被毒打致死之恨的发泄。经历了这么多人生磨难,大姑坚强得像一块钢,从此,再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我听着大姑的故事,为她擦去眼角的泪水。可悲的是,大姑说不清她的男人在八路军的哪个部队,在队伍里担任什么职务。更可悲的是,解放后,政府有政策照顾安置军烈属,可是必须得有人证明。姑父的战友大都不在了,即使有人活着,大姑也叫不上一个名字。就这样,大姑连烈属都不是。
四
解放后,大姑带着女儿嫁到谢杖子谢家。谢氏姑父因成份不好,适龄婚娶了却还未有人家提亲。大姑不嫌他成分不好,姑父也不嫌弃大姑带个孩子。就这样,两个人结婚了。大姑嫁到谢家又生了两儿两女。我们这次去看大姑,才知道姑父几年前过世了。姑姑的两个女儿都是高个儿,大眼睛,灵秀,二儿子浓眉大眼。在见到大姑的前一夜,我们住在秦皇岛市榆关镇榆关村大姑的二女儿家,二女婿讲了一个谢氏姑父的故事。大姑家孩子多,生活困难,有一年过大年,身为村长的姑父给人家杀猪,人家要给他一块精肉,姑父说:“我要那个猪头,这样孩子老婆都能吃一顿。”可见当时日子之难,也可见姑父的勤俭持家。
大姑的房子低矮阴暗,没有电视电话,没有现代时尚的摆设,却有四组老式红柜,大姑说:“你姑父种了很多粮食,装满了八节红柜,他去世前跟我说,我死了也放心了,这些粮食够你这辈子吃了……”我再一次为大姑的故事流泪。因时间有限,我对谢氏姑父的故事还没了解太多,听大姑说他生前一直做村长,他做村长一点也不贪,耿直公正,村里人都很怀念他。
五
1943年,爷爷组织家人迁徙,最终落脚在一个叫伙房的村子,即现在的巴林左旗花加拉嘎乡伙房村。
两辆绑着架杆的马车上装满了必备家什和包裹,老弱婴幼儿坐在包裹上,其他人只能步行。父亲那年才七岁,因为是男孩子也没有坐车资格,只能跟着迁徙的队伍跑。跑了几天后,父亲丢了。
七岁的孩子丢了,迁徙的队伍又不能返回去找,生死只能靠他自己。父亲在从内地向东北迁徙流亡的队伍中找到一个盲人为伴。盲人吹曲算命讨得几文钱两,父亲给盲人引路混口饭吃。迁徙的队伍走走停停,天黑了总会在一个地方停下来讨饭休息过夜。有一天早晨,队伍正装车待发,忽然听到路上传来笛子曲儿,人们停下来看,父亲的大哥说:“那个领着盲人的怎么像三头?”就这样父亲又回到家人身边。时间快过去一个世纪了,大姑还清楚记得几个弟弟的乳名。“你大爷叫大头,二大爷叫林头,你爸叫三头……”我泪如雨下,父辈的乳名没有几个人知道,特别是我们晚辈。大姑啊……虽然从来不曾提起,其实从来未曾忘记。
大姑骄傲地说:“我是老党员呢!”然后小声地问我,“老侄子,你是党员吗?”
“是!”我回答道。
大姑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你看我这记性,老侄子是记者,哪能不是党员呢?党员好啊,能约束自己,心里有别人,能为别人谋福利!”
听着这些话,我有些惭愧,也有些激动。
2019年,大姑去世了,走完了她坎坷而又平凡的一生。
我为姑姑点赞:生命的乐章,即使是苦难,也仍然有不屈和顽强的音符;苦难的土地,仍然可以盛开出芬芳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