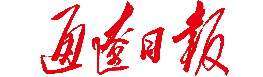●王玉玲
村子是忙碌的,也是生机勃勃的。房檐上的鸽子和院子里的鸡、鸭、鹅,它们欢快地叫着。等到呼啸的西北风彻底把村庄陷入沉寂,裹进空闲时,凌厉的猪叫声便会响彻村里——刚刚进入年关,大家争先恐后开始杀年猪了。四叔家喂的猪比别人家的更肥硕,杀得也更早。我一趟趟去柴垛边帮着四婶抱柴火。在柴火垛下面,发现了那三个委委屈屈的鸡蛋磙子。拽走木柴,三个鸡蛋磙子暴露在阳光下面。轴心轴碗都在,只是木框让柴垛给压断了。
那些年的春天,路边的杨树叶子都变得翠绿一片时,该耕种了。父亲套着家里那匹温顺的白马,开始种地。锋利的犁铧子翻开泥土,犁出垄沟,母亲和另外三两个女人熟练地把种子点进垄沟。低头播种的乡村女人带着对土地的虔诚和信仰,把饱满的种子从手指间滑落进泥土里,一个木钵梭把蓬松的垄背土均匀地划进垄沟,覆盖住种子。姐姐牵着一头小毛驴,后面拖着三个鸡蛋磙子。鸡蛋磙子吱呀吱呀地在垄沟里滚动着。压实土不跑墒,就能抓好苗。天很高很蓝,我们一群小孩子在田埂上挖野菜,头顶有鸟清脆而愉快的叫声,空气里有犁翻开泥土时断根蒿草的清香,一切都那么生机勃勃。
多年之后,我客居于一座小城,空气中弥漫着呼啸而过的烟味,以及早晨大暖烟囱中散发的煤烟味。回想起家乡田野上空高远的蓝天、清渺如烟的云朵和那些咯吱响动的鸡蛋磙子,美好的乡村宛如裹挟着蒿草清香的田野之风,扑面而来。我决定收集一些乡村的老物件,把乡村的老时光都拉回来。
那三个鸡蛋磙子,连同折断的木框都被我“鼓捣”回来,放到了北面沿着小菜园的墙根下面。那片小菜园子,新匀出了两个池子来种花。将蝴蝶花籽拌入白菜籽中,同时在芫荽池里也撒上一些,还在从母亲菜园移栽过来的菇娘附近同样撒上一些。菜园不光种菜,也要种花。夏季,菜园里的白菜长大了,芫荽也开出细碎的白花,那些蝴蝶花有七八种颜色,一朵朵花蕾探出来,随后便五彩斑斓地绽放了。有风刮来,真的像一只只翩翩飞来的蝴蝶。在我们单调无趣的生活中,种上点有色彩的花,心情就有了调剂,一边种着柴米油盐,一边种着花朵云烟。
在南墙根的陈年木柴垛下面,又找到个碌碡。收获的高粱、大豆、谷子都得把包裹的壳碾碎,才能露出温暖盈润的米,所以都要用这个碌碡反复地碾压。然后在场院里趁着欢实的西北风猛劲地吹来时,一群壮汉开始扬场,把稻壳扬出去,那些饱满的粮食就能收进仓房。播种、收割、拾穗,在厚重的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每一粒粮食都是用汗水浸泡的。这个碌碡的作用不止如此。科尔沁风沙大,干旱水分流失快,翻好的田地用碌碡压平压实,水分就被锁在地下了。多少年来,碌碡已被弃置一旁,寂寞地躺在柴垛之下。不妨让它依旧卧于南墙根,在院子里为它保留一方空间,让它见证乡村的沧海桑田。
在农耕文化里,这些石器把人类从手脚并用的耕作中解放了出来。一代一代的农耕器具在进步和更新着,从木质到石质到铁质农具的演变,唯有这些石质的农具不会腐化和生锈,也能经历时间的风雨。
又在四叔家的北窗台,看见个煤油灯。那煤油的气味还在,乌黑的灯盏上满是污渍和时光的沧桑。我和四姐夜晚趴在如豆的煤油灯下,看那本叫《潘多拉的匣子》的小人书,那些神话里的精灵在一个乡村小女孩的心里飞进飞出,飞过简陋的房间,飞出暗夜。挤在微弱灯火下面,让四姐讲着书里面结局美好的童话故事,漫长的冬日夜晚便在故事里慢慢变亮。
四婶早已嫌这个肮脏乌黑的煤油灯碍事,看见我垂涎的目光,就装在一个塑料袋子里送给了我。回到家,晚上熄灭了所有明亮的灯,点燃了这个煤油灯灯芯。豆粒大的火苗飘忽弱小,哪能承载一个屋子的光明,那煤油的强烈气味熏得我顾不得怀旧,赶紧把它熄灭,点亮电灯,璀璨灯火的光明铺天盖地而来,重新回到一个光亮的世界。随后把它装好,放在了后库房的一个架子上。
我“觊觎”着老李家做豆腐的那个石磨。现在这个石磨早已经像一个年迈的老人在墙角下消磨着时光。那一年过年时,母亲把泡得鼓胀胀的黄豆,拎到了老李家。李家大叔套上毛驴,把黄豆磨成豆浆。那些淡黄色的豆浆从石磨流下来,流到底下的大盆里。在大铁锅的熬制下,李大哥还给我和母亲一人盛了一碗豆浆,香浓的豆浆至今还留有余味。点好卤水,压在豆腐盘子里,水嫩的豆腐就成型了。我们这些小馋鬼,在豆腐的热气还没有散尽时,便用农家大酱拌上小葱,惬意地享用着。前些日子听母亲说,李家大叔去世了。脸上总是挂着笑容的李家大叔口碑很好,总是那么温温和和的,遇到村里的小孩子也是笑容可掬的,小时候过年的记忆似是和李家大叔清香的水豆腐连在一起的。
东院的巧手嫂子会做布老虎枕头,各种形状的,栩栩如生。七八年前我和东院的老嫂子学会了做布老虎,在集市上买回如同老虎皮一样的棉布,按着样子裁剪好,玲珑的耳朵、摇曳的尾巴、粗壮的小腿也是充满情趣。我跟嫂子说,做几只精致的布老虎摆到展厅里,就称得上民间艺人了。老嫂子对此只是付之一笑,说道:“闲时做两个送你,可别摆到什么展厅里让人笑话了。”
曾经看过的黑白电视,还有在墙壁上滴答作响的老挂钟,都已被我妥善保存起来了。收废品的汽车在门口吆喝着,也会来到院子,问我卖不卖旧电视和旧挂钟。别人哪里知道,它们在我心里无论怎么陈旧,其怀旧价值都永远存在。那个旧电视是我最初看到世界的一个窗口,外面多彩的世界在那个小小方寸的屏幕上变幻着,是我生活的村庄以外的世界。在漫长的冬日夜晚,大家都在炕上发出轻微的鼾声,我还因为白天某个老太太的鬼怪传说而心里恐惧着,西墙上挂钟不紧不慢地滴答着,每过一个小时,就“当”地敲响一下。四姐对胆小的我说过,黑暗的夜晚,每过一个小时,天使就会飞进挂钟敲一下去看护那些胆小的孩子。四姐脑子里有那么多学问那么多故事,她的话哪能不信呢!聆听着母亲轻柔的鼾声,仿佛那鼾声也在哄我入眠。伴着滴答作响的钟声,我缓缓进入了梦乡。
我的乡村小博物馆就这样酝酿着,收集着。孩子是一个最好的参观者,他对这些用途不明的物品满怀好奇。旧的和新的交替进行,如同你不知道什么东西又把什么东西取代,如同青春和暮年的交替。在岁月的长河中,所有的人和事都将成为影子。
陆续去收集那些老村庄的影子,让一些人写过的文字,一些人用过的器具,都留存着生活过的信息。欣喜也好,陈旧也罢,都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