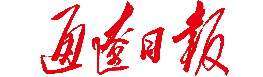□刘宏杰
一个宁静的午后,楼后窄街传来叫卖声“烀苞米,新出锅的热乎苞米……”那声音由远及近,又渐渐模糊,最后彻底消散在风中。随着远去的叫卖声,我的思绪竟不由自主飘回到儿时。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老百姓大多住平房。我家所在的片区民房密集,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足有七八百米长。有人的地方就有买卖,那会儿总有走街串巷的小商贩,胡同里不时传来各样叫卖声,也成了那些日子里鲜活的底色。
“冰棍啦!”炎炎夏日里,这声吆喝对孩子们有着极大诱惑。那时老百姓家没几台冰箱冰柜,孩子想“凉快”一下都难。卖冰棍的商贩在“二八”自行车后座上绑个木头箱子,里头裹层保温棉被,这自制“冰箱”能让冰棍几小时不化。不管男女,喊“冰棍啦”的声音都特有穿透力,还故意把“啦”拖成二声,透着股滑稽。孩子们一听见叫卖声,早早就候在门口,掏出家长给的零花钱买一根——那时就两种冰棍,一毛钱的水果味,两毛钱的奶油味。可对孩子们来说,不管哪种,能含在嘴里都是顶开心的事。后来,有冰箱的人家多了,胡同小卖铺也多了,不知从哪天起,那声“冰棍啦”就再也没听过。
“豆腐!”得听准了,是“豆fē”——我们这儿卖豆腐的总这么喊,两个字能拉出十个字的绵长调子。过去卖豆腐的没固定摊位,想买全凭运气:有时胡同里一天能听见两三回,有时一两天都没动静。商贩同样在“二八”自行车后座上固定个木质方盘,豆腐切好块,上头扣张塑料布,脖子上还挂个哨子,往往哨声先到,叫卖声随后才来。有意思的是,街坊远远听见“豆fē”,赶紧抄起盘子或小盆奔向门口,也喊一嗓子“豆fē”应和。我记事起,豆腐两毛一块,现在涨到两块钱了。如今那声“豆fē”,在早市偶尔能听到,平时难寻踪迹。
“糖葫芦,冰糖葫芦!”这声吆喝得等天冷了才能听到。跟卖冰棍、豆腐的不一样,卖糖葫芦的不爱钻胡同,更爱在街上找个固定地儿,或是骑车载着糖葫芦,往人流密集的地方去。车把前绑根木棍,顶端扎着厚蒲草,红彤彤的糖葫芦就插在上头——带籽的八毛一串,抠籽的一块一串。说实话,那会儿糖葫芦做工粗糙,也不算卫生,可一个冬天能吃上几串,就开心好几天。后来,卖糖葫芦的从自行车换成带棚电动车,糖葫芦也不只有山楂了,猕猴桃、草莓、橘子瓣挨个往上串,就连传统山楂的口感都变好了,还裹上了干净包装。如今冬天街头,“糖葫芦,冰糖葫芦”的叫卖声仍此起彼伏,只是早没了真人吆喝,全是扩音喇叭里的录音。
“磨剪子嘞、戗菜刀——”过去磨刀师父的吆喝,也是胡同里的常客。干这行的多是满脸风霜的老人,他们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车后座驮着全套家当:一条窄长的木凳、几块粗糙的磨刀石、转起来“嗡嗡”响的砂轮,还有些缠着手帕、叫不上名字的小工具。谁家有生锈发钝的菜刀、剪子,递到他手里,那双爬满老茧的手便熟练地打磨起来,没一会儿工夫,原本黯淡的刀剪就变得锃亮锋利,又能接着为一家人“效力”了。
除此之外,过去崩爆米花的、卖鲜牛奶的、收废品的,都有各自的叫卖声,它们都曾是生活里的常客。可时至今日,这些叫卖声要么彻底消失,要么越来越少见。人到中年再回想,才发觉那些藏在吆喝里的旧时光,原来是那么珍贵、那么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