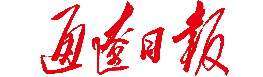●草原公主
扎鲁特的风总在黄昏时分苏醒。它裹挟着特金罕山的松香,掠过草甸低垂的云絮,终落于褪色的屋檐一角。暮色中,墙体静默如一枚被岁月磨旧的铜钉,将春秋楔进斑驳的砖缝深处……
泥土里的年轮
故乡的坐标,该从鲁北镇北沙包最高处的这座老平房说起。南墙的砖缝里嵌满经年的苔痕,北边的杨树早已比记忆中粗壮,树影斑驳处,是连绵的庄稼地在风中起伏,恰似母亲手中织针勾织的云纹——那些毛线编织的暖意,曾暖透无数个北疆的冬夜。
父亲去世那年的冬天,北沙包的雪下得格外厚。光秃的杨树枝桠,在窗玻璃上投下铁画般的剪影,斑驳如未解的谶语。那时我总以为,死亡是一场漫长的告别,却不知故乡的泥土里,早把人事兴衰酿成了年轮。就像南宝力皋吐的古墓群,那些陶型圣母与高领双耳壶,在沙土高岗下沉睡数千年,终于在某个清晨被考古队的探铲唤醒,让松辽分水岭的风,又带回了新石器时代的渔猎号角。
坍圮的金界壕夯土墙仍固执地趴在浅山草原上,用残缺的马面与壕堑,向每一阵掠过的风讲述金朝的烽火。让我忽然懂得:所谓故乡,原是历史在现实中投下的叠影,每一粒沙尘里都藏着文明的密码。
乡音里的经纬
母亲的乡音是东北方言与蒙古语的交融。她织毛衣时哼唱的小调,前半句是科尔沁次方言的低吟,后半句便滑入东北话的悠扬,像勒勒车碾过草甸时的吱呀声——颠簸处似马蹄踏沙,平缓时如溪水穿林。那些年,她在经销部拨响算盘的噼啪声,与街角小贩的吆喝声交织,织成了鲁北镇清晨的独特经纬:卖奶豆腐的老汉用蒙古语拖长调子,卖沙果干的大婶操着方言讨价,百灵鸟在电线杆上跳跃啼鸣,乌力格尔的四胡调从蒙古包里漫出来,在车辙印上蜿蜒成河。
父亲走后,母亲的手愈发精巧。她绣的盘锦鞋面上,山杏花与鹿纹相依相缠,那是扎鲁特刺绣里最质朴的意象。有次在通辽的商场,我见着机器绣的蒙古袍,花纹繁复却失了生气,忽而想起母亲在昏黄的灯光下穿针走线的模样——她总说,针脚要顺着布料的纹路走,就像人得顺着故乡的节气活。
格日朝鲁的牧民仍在走“敖特尔”,他们的勒勒车辙印,在草原上画出的弧线,与母亲手中的绣线一样,永远牵着这片土地的魂。
时空里的守望
记忆里,关于西辽河文化的描述总显得遥远而抽象,直到站在阿木斯尔遗址的沙丘上,才真正触碰到五千年前的时光碎片。磨制的石斧还带着先民手掌的温度,“之”字纹陶片上的每一道刻痕,都是岁月未曾风化的方言。
离开北沙包二十余载,最难忘老屋墙上那幅泛黄的扎鲁特版画。画中牧马人扬鞭疾驰,粗犷的线条里藏着“留黑”阳刻的力道。纸色已褪成秋叶,拓印的轮廓却依然鲜活,仿佛能听见木版与拓纸相触时的沙沙声。如今想来,那些拓印的岁月与母亲的织锦,原是同一种守望——前者以刀为笔记载历史,后者以线为墨编织岁月。就像大黑山的人面岩画,圆目微张的神情穿越千年,与故乡的云影天光相映,让每个凝视者都忍不住猜想:在我们之前,有多少代人曾站在同样的山岗上,看季节轮回,听草木荣枯?
去年陪母亲回北沙包,她在杨树林里站了很久。树影婆娑中,她轻声说起父亲去世前那个春天,曾为一棵棵杨树修剪枝桠。“那时他总说,等你们长大了,这林子就该成材了。”母亲的声音轻若一片落叶,却让我看见时光在年轮里打转——当年的小树早已参天而立,父亲的坟头也开满山丹花,而穿越时空的风,依旧徘徊在辽代豫州城的残垣上,将庙宇遗址的碎瓦吹成了一首无人能和的长调。
写给故乡的信
此刻在通辽的住所,窗外霓虹如星子坠落,却照不亮远处原野的轮廓。案头摆着从老家带来的奶豆腐,乳香醇厚的方块在瓷盘里泛着温润的光泽。咬一口,微微的酸裹着淡淡的甜,恍若故乡的方言——初听粗粝,细品却满是温情。母亲蜷在沙发上织毛衣,毛线团在她膝头打转,像极了格日朝鲁草原上低垂的羊云朵。
城市的钢筋水泥缝隙里,再长不出野韭花的白雾,也听不见勒勒车的木轮与草茎摩挲的私语。母亲常说,人像候鸟,迁徙得再远,翅膀上总沾着故土的霜。我忽然明白,所谓乡愁,从来不是简单的眷恋,而是血脉与土地的共振——是远古的陶片沉睡于掌心的重量,是千年的刻痕烙入瞳孔的纹路,是母亲织就的每一朵云纹里,藏着的整个北疆的春秋。
北沙包的风又起了吧?它掠过杨树梢,掠过庄稼地顶,掠过母亲当年经销部的旧址,最终伏在了窗台前。恍惚间,风声与母亲的针脚声重叠,似叩问着岁月辙印深处:这跨越千年的守望,是否早已在时光里,织就了永不褪色的年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