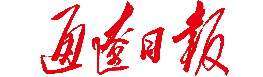●史艳茹
父亲无心插下的文学之柳
我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如今能成为一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民教师,与父亲潜移默化的读书写字不无关系。父亲是一位有着7年军龄的退伍军人,退伍后一直生活在农村,或许因为他曾是空军地勤话务员的缘故,特别爱看书,写得一手好钢笔字。在我的记忆里,当时村里有红白事,写字的活计总由父亲来做。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农村人都在忙着农活,即使农闲,也要做些盖房搭屋、编筐窝篓,或者挖药材、砸树墩的活。我父亲在做这些活外,还经常做两件事:一是看书,特别是武侠小说;二是写字,只要有空闲,父亲就会在我们用过的书本或是过年糊墙糊顶棚剩下的报纸上练字,写的内容,完全是随心所欲,有的是从报纸上看到的,有的是记忆里的,有的是随时随地感慨的。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父亲写的内容是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香香公主;东邪黄药师、西毒欧阳锋;南慕容,北乔峰;江南七怪恶贯满盈,四大名捕(无情、铁手、追命、冷血)震关东。忽然间觉得这些内容很有吸引力,我悄悄地翻开了父亲不知从何处借来的封皮掉落、纸页泛黄的一本书——《书剑恩仇录》,我一下子被书中的内容深深吸引。从此,只要父亲不在家,我就偷看。不知不觉中,我看过了父亲借来的好多书,《七侠五义》《白发魔女》《七剑下天山》《天涯明月刀》《虾球传》等。同时也零散记得一些对不上作品的人名,像西门吹雪、老顽童、天山童姥、灭绝师太、达摩祖师;还记得一些对不上人的功夫绝学,如一阳指、六脉神剑、降龙十八掌、丐帮打狗棍等。或许是小说内容太精彩,我沉迷其中,抑或是那时的我精神世界太贫瘠,总之,我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书。这些书充实了我的童年时光,也无意中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文学世界的门。
影视剧绽出的文学之花
上世纪80年代,改革春风吹满地,农村也迎来了新气象,电视机渐渐走进农村家庭。我们村里有了两台电视机,每天,那两家里来观看电视的人都爆满。夏季就把电视放到窗台上,院子里挤满了人,为了看电视,大家根本不顾蚊虫叮咬,只是点一段火绳或让孩子们拔点蒿草点上熏蚊子。有时主人家闹情绪,电视不开,大家急得乱窜,仿佛不看就丢掉了什么,更有甚者,会不顾天黑,到二里地远的邻村去看。我也曾随波逐流地去过,看的是《纵横四海》。我也曾“殷勤”地帮人家做这做那,为了在人家插门前进去,能有一个相对好的位置看电视。
爸妈一向勤劳节俭,不久后家里买了第一台熊猫牌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从此来家里看电视的人络绎不绝,那时白天没有电视节目,除非是正月里,初一到初八白天有电视。那些年,正月里电视剧都是一天四到八集连放,没有广告,看着那才叫过瘾。那些年,没有补课班、特长班和各种艺术兴趣班的我看过《霍元甲》《陈真传》《精武门》,看过《楚留香传奇》《侠客行》《雪山飞狐》《法网柔情》《人在旅途》《外来妹》《血疑》等,认识一些港台明星和外国明星,特别是日本电视剧《血疑》不仅让我知道了明星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还知道了一种特殊的血型是Rh阴性。
高中时期广植文学之树
虽说已是不惑之年,我依然相信,与文学结缘是冥冥之中的一股力量在推动。上世纪90年代,我在初中学校老校长的建议和帮助下,有幸到县城读高中。当时学校周围有许多电话亭,兼卖各种报刊杂志,还顺便租书。或许是大家的能量场相同,我所在班级的同学都是爱读书的人,我们一商量,决定一起交换着看。一本书,三天之内租金五角钱,我们紧一紧时间,三天就能看三四本,大家如饥似渴地读着。我读过席娟和琼瑶的一系列言情小说,特别喜欢琼瑶的作品,有《却上心头》《心有千千结》《梅花三弄》……那时她所有能租到的作品,我们都看了个遍。功课越来越紧,没时间看长篇,我们就打起了《读者》《青年博览》的主意。政治课换书看,语文课也换书看,看书的速度飞快。我们成了附近电话亭、租书摊的常客,还积累了预订和延期还书的信用。学习任务越来越重,距离高考越来越近,我们把读长篇小说改成读短篇故事,后来又压缩成单篇文章。可租书摊老板传来的新书上市消息,还是让我们心里痒痒的。好在那时出现了一种快捷的阅读形式——录像厅,它们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县城的大街小巷都挂出了新片播放的通知。我和几个同学省下饭钱,去看了《泰坦尼克号》《乱世佳人》《魂断蓝桥》《星语心愿》《妈妈再爱我一次》,每一部影片都足够精彩,直到现在我还能记得一些精彩片段。高考结束后,有一段空档期,我报复性地读了金庸的一些小说,知道了他的十四部经典之作可以简记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高中时期读的书五花八门,读书的形式也多种多样。至今我还在内心窃喜,想起同学海霞在语文课上看《上错花轿嫁对郎》时,失态笑出声的场景。
大学徜徉文学乐园
千禧年,我如愿迈进大学校门,选择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终于可以畅游文学伊甸园。第一次走进图书馆借阅时,我被两层楼高的书架惊呆了,一次性借了能借到的所有书。从那时起,我成了图书馆的常客,我曾为《平凡的世界》里努力想要挣脱贫穷束缚的孙氏兄弟感叹;读了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还读了许多外国作品,如《德伯家的苔丝》《简爱》《红与黑》,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大学期间,我如同一个“饥不择食”的文学乞丐,有机会就看书,什么类型的都读,反贪涉黑、言情武打、刑侦心理、散文诗歌。也是在那个时期,我读完了《红楼梦》并完成大学论文《红楼梦之黛玉的悲剧人生》。
虽已走出大学校门20多年,我还能清楚记得校园租书亭的那件趣事。
一个雨天的傍晚,我到宿舍楼下的租书亭换书,一个男生和书亭主人的对话,把我笑到喷饭。“怎么没看到呢?”男生说。“你找什么书?”书亭主人问道。“《我是你爸爸》”,男生说。“我还是你爷爷呢”,书亭主人生气地大声说。我和那个男生一起笑了起来,书亭主人很生气,“都大学生了,也不知道尊重人,我又没惹你,干嘛张嘴就骂人。”借书的男生看了看我,我们再次大笑。“他没有骂你,那是王朔的小说名字”,我说。书亭主人脸一下就红了,不住地给男生道歉。
与文学渐行渐远
师范大学毕业后,我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教师。如今,已是拥有20多年教龄的“老教师”,但是却成了文学阅读的流浪者。参加工作的前五年,职场小白,无力应对教育教学的各种事物,把阅读搁置;成家之后,带娃、工作、做家务,分身乏术,静心读书成了奢望。最近十年,更是忙得焦头烂额,接送两个孩子上学,洗衣做饭,上班,家务劳动越来越多,先生在外地工作,读书更是无从谈起。忽然间觉得自己现在就是被文学列车丢下的孩子,眼见它渐行渐远,渐无踪。20多年来,说起来有些遗憾,虽说在努力教书育人,但是精神世界被尘世荒芜。好在无论出差旅游,还是走亲访友,只要去外地,买书的习惯还在,家里有好多我上班后从外地直接背回来的书,或许这是一种精神补偿吧。直到去年,看到在短视频大火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我终于没忍住买了一本,断断续续地看了好久才看完,最后的酋长落幕了,鄂温克族下山了。今年李娟的《我的阿勒泰》火出圈后,我也没能免俗,跟风买了一本,至今还没读完。看到沈老师发的同题习作通知时,我内心五味杂陈,有早年间畅快阅读的喜悦,更有成家立业后被迫放下挚爱(阅读)的遗憾和不舍。看着那一本本没怎么翻阅的新书,失落无奈充斥在内心。我在期待追寻挚爱的时机,明年姑娘高考,儿子读初中,估计能抽出一些时间来读书了,弥补这20多年来欠下的阅读债。现在,我能更深切地体味成年人世界有太多的身不由己。
如果非要我回答与文学的距离,我想用曾经的相伴而行、后来的渐行渐远、现在的期待“重逢”来回答是最恰当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