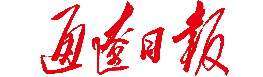□吕艳华
科尔沁草原的风里,总飘着牛铃的轻响。那声音像时光的年轮,一圈圈刻在我记忆的深处。每当暮色漫过草甸,我总会想起父亲暮年时摩挲着牛犊额头的手,那双手布满老茧,却比任何丝绸都温柔——它们曾托起科尔沁黄牛的黎明,也托起了我整个童年的仰望。
雪夜车辙里的星光
1978年的冬天,科左后旗的雪下得格外沉。三辆载着西门塔尔种牛的卡车碾过冰封的土路,像三枚火种落进沉寂的草原。父亲从扎兰屯农牧学校毕业不久,墨绿色的工作证还带着油墨香,却已在畜牧兽医站的木屋里熬红了眼。那些日子,单位的草棚成了他的第二个家,他总说种牛是“金疙瘩”,得用养孩子的心思伺候。
我对父亲的工作最初印象,是挂在墙上的牛皮笔记本。泛黄的纸页上画满了牛的骨骼图,标注着“冷配技术参数”的字迹被手指磨得发毛。那时他常下乡“蹲试点”,一去就是数月。有年深冬,母亲抱着发高烧的弟弟在卫生院掉眼泪,托人捎信到巴彦茂都苏木,可信息在雪地里爬了三天才到。等父亲裹着一身风雪冲进病房时,弟弟的烧刚退,父亲冻裂的嘴唇哆嗦着,只说了句“牛犊接产完了……”
更让我心惊的是那个爆胎的冬夜。父亲和同事的吉普车抛锚在荒滩,零下三十度的风像刀子割脸。他们背着工具箱走了十几公里,脚底板和冻硬的皮鞋粘在一起,每一步都扯得血肉模糊。后来是牧民的四轮车把他们拖到村里,等到单位的救援车时,父亲的耳朵已经冻得发黑。母亲给他抹冻疮膏时哭了,他却咧着干裂的嘴笑:“没事,比当年给牛接生时冻的那回强多了。”
那些年,父亲的团队像一群拓荒的骆驼。百姓不理解冷配技术,觉得“洋牛”配本地牛是瞎折腾。有牧民牵着两年没受孕的母牛堵在单位门口骂街,父亲就蹲在牛圈里一待一整天,翻出牛粪查看排卵情况,用蒙古语跟牧民比划着解释。他常说:“咱不能只懂技术,得让老乡看见实实在在的好处。”
草场上的科学诗
父亲的办公桌抽屉里,藏着一叠泛白的奖状。最珍贵的是1985年那张,自治区政府颁发的“科尔沁黄牛培育成果奖”。可在我眼里,那些证书远不如他笔记本里的草图生动——画着西门塔尔牛与蒙古牛的杂交谱系,像一棵生长在草原上的生命之树。
记得有次他带我去试验田,蹲在草地上扒拉牛粪。“妮儿你看,这粪里有学问呢。”他捡起一块捏碎,指着里面未消化的草茎,“好牛吃得多消化好,粪便里草渣少。”那时我不懂什么叫“乳肉兼用”,只看见父亲蹲在牛群里,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尊守护草场的雕塑。
培育的关键期,父亲和同事们发明了“三系配套”法。他们在不同苏木设试点,给母牛建立档案,像照顾新生儿一样记录发情周期。有回半夜暴雨,父亲冲进牛棚给待产的母牛搭遮雨棚,自己淋成了落汤鸡,却笑着对发抖的牛犊说:“你真牛!出生就顶着风雨,将来一定会长成壮壮的。”
最难忘的是“科尔沁黄牛”命名那天。父亲捧着红头文件回家,眼里的光比煤油灯还亮。他把文件铺在炕桌上,用手指一遍遍描摹“中国西门塔尔牛——草原类型群”的字样,突然扭头对我和弟弟说:“记住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整个草原的心血。”
牛铃摇响的传承
如今的科左后旗,早已是“黄牛之乡”的代名词。阿古拉镇的牧场上,上万头科尔沁黄牛像流动的黄金;巴胡塔苏木的养殖大户家里,单头牛能卖出二十万的高价。每当在新闻里看到“104万头存栏”的数字,我总会想起父亲当年在油灯下计算配种率的背影。
去年回草原,遇见一位养牛合作社的大姐。她指着圈里油光水滑的母牛说:“当年你爹教我们冷配技术时,我还是个扎辫子的丫头呢。现在我这合作社,一年能出栏三百头牛!”说着她递来一碗热奶茶,杯沿映着远处牛群的剪影,像极了父亲老照片里的场景。
父亲退休后,总爱拄着拐杖去村口的牛棚转。有次他摸着一头初生的牛犊喃喃自语:“长得真壮实,比当年第一头改良牛强多了。”阳光落在他斑白的头发上,牛铃在远处叮当作响,像一首悠长的草原牧歌。
上个月整理父亲的遗物,在木箱底发现了一本褪色的相册。第一页是1978年那三头西门塔尔种牛的照片,牛眼在黑白胶片里闪着光。最后一页是去年我带他去参观现代化牛场的合影,他坐在轮椅上,身后是整齐的智能化饲喂设备,脸上的笑容比草原的晚霞还灿烂。
科尔沁的风还在吹,牛铃的声音穿过四十年的光阴。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就像当年那三头种牛,把科学的火种播撒在草原深处。如今这火种已成燎原之势,照亮了牧民的“牛”日子,也照亮了我心里那片永恒的牧场。每当想起父亲在雪夜里跋涉的背影,我总觉得,那些印在草原上的足迹,早已化作了牛铃里的星辰,永远在科尔沁的天空下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