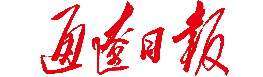□张亚萌
许多年来我看书有个喜好,拿起什么书,凡是读得入迷了,便要遍处搜寻作家的人生图幅来反复打探瞧瞧。
读着《撒哈拉的故事》,读完《稻草人手记》,要打开夹杂在书卷里那张赠送的三毛照片来仔细端瞧。是一张生活照,她倚靠在一座枯槁植物旁叉着腰。我顺势移下手边的台灯,将橘黄色的光打在一处,霎时照片中狂风四作,黄沙卷集迎面扑来。
在长到后跟的红色粗布长裙里,三毛也许是在笑。两抹浓黑的眼影掩映着眼眶,让人难以分辨出她眼光流露的神情。我猜她必定是刚刚从远处打水回来,因为她翘起的左脚大脚趾上沾到了几点干泥巴。
在烈日鸿晖中,我们攀上她家门口的那座沙山,蜷起双膝诉说起哭泣的骆驼,还有爱情飞蛾扑火时的快乐。
这一晚,我决定再光着脚和她走上一段,再穿越一次青春与冒险的险滩,毕竟陷在沙丘里的绵软让我舍不得说再见。
春天来了的时候,我便会坐地铁去到地坛,听听雍和宫内回荡不绝的钟磬声,最后再绕回地坛。
“是铁生的书,铁生已经不在了。”铁生已经不在了,经年绕过的车辙还在,母亲寻他的脚步声也还在。“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
每夜每日,他独自陷在此处,在我清晨到达时告诉我远处有一片蛮荒的原野,神光甚至也少照耀;当浓荫蔽日压制心头,他摇晃手中那枝柏给我看,我又听见他说起:“——有一年,十月的风又翻动起安详的落叶,我在园中读书,听见两个散步的老人说:‘没想到这园子有这么大。’我放下书,想,这么大一座园子,要在其中找到她的儿子,母亲走过了多少焦灼的路。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
没人说读书就要正襟危坐,我就不太喜欢。若是读书,我喜欢选在傍晚回家的路上,寻一处僻静躺椅背对着夕阳坐下,了却一天的忧心事,存下一天中最后的暖意,翻看几页《济南的冬天》,听老先生讲一个响晴的冬天里有山有水的老城是怎么睡着、又是怎么醒来的;要是到了盛夏的夜晚,总该伴着虫鸣声盘腿读读泰戈尔的诗集。万籁俱寂中人可通神,也许我的心正是旷野的鸟,在你的眼睛里可以找到它的天空。
毛姆说,“我从来都无法得知,人们是究竟为何会爱上另一个人,我猜也许我们的心上都有一个缺口,它是个空洞,呼呼地往灵魂里灌着刺骨的寒风。”
始于一页,抵达世界,我想我们始终要敬畏,敬畏我们尚且不知道也无法去琢磨的东西。不然该怎样解释总有一些人的灵魂,会在你读到某句话、某个词的一瞬间,从平行宇宙中穿越千年击中你的心脏来到你面前,拱手送上那把解开迷惑你许久的问题的钥匙?他们让你流泪,又为你拭泪,我们为了交下这样一个朋友而欢心感动,默然并开启属于自己终身的浪漫。
也许我们读书,而后知道自己并不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