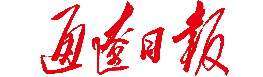文/杨丽琴
傍晚时,晚霞悬在西边的天空,如铺开一匹绚丽的锦缎,空气中飘散着阵阵稻谷的香味儿。
村子里忙碌起来了,家家屋前的谷场上,撮的、扫的、扶的、拉的,如一幅幅乡间农忙民俗画。大人们一脸喜气地说笑,嗓门都大了几个分贝。“我家今年肥力拔上来,最起码也能收一千多斤”;“我家防病治虫及时,没有受到伤害”;“今年收成都好,抓紧晒干了,打点新米过中秋”……
父亲停下手里的活,抓一把稻谷,眯着眼睛,在手心里掂了掂,又把稻谷放进嘴里轻轻嗑着,只听“咯嘣”一声,稻谷裂开了,父亲吐出稻壳,慢慢咀嚼着清香的稻米,一脸的虔诚和欢喜。
孩子们个个脏兮兮的,像从灰土里扒出来似的。懂事的帮着大人收稻谷,小大人似地忙前忙后;调皮的像散了绳的小牛犊,有的把稻谷当成了“溜冰场”,赤着脚在上面“哧溜溜”地滑冰;有的把垒起的稻谷当成“防护墙”,手指折成枪,嘴里“嘟嘟嘟”“哒哒哒”玩打仗游戏;有的好似人来疯,围着稻谷“嘻嘻哈哈”追逐嬉闹。晚归的鸡和鸟儿也来凑热闹,“咕咕”“唧唧”大着胆子在稻谷旁边吃大餐。
这时的大人们脾气特别的好,他们只专注着手里活儿,偶尔,瞥一眼孩子们,叫一声,“别闹,别处玩去。”偶尔,对着鸡或者鸟儿噘一噘嘴,“去!真会偷嘴。”便继续忙手里的活,而孩子们好似没听见,鸡们鸟儿们只轻轻掀了掀翅膀,自顾自地吃着。
唐代李绅《悯农》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春天,从一粒种子下地,在农人的期盼里,孕育、发芽、长出嫩绿的青苗。再在农人的养护下,一点一点地长大、成熟。金色秋天到来,稻谷在秋阳下散发出璀璨的光泽。村民们握着锋利的镰刀,收割着一行一行稻谷。
那时,上小学的我,一放学便丢下书包,挎着篮子下地拾稻穗。母亲在前面挥镰收割,我跟在后面,捡拾遗落的零星稻穗。父亲负责挑稻把,他将一捆一捆稻把码在稻架上,扎紧,弯下腰,担在肩膀上。父亲直起腰板,竹木扁担在肩头渐渐变弯,像挂在天边的一弯新月。
稻把全部挑到谷场上,开始脱粒,父亲牵着老牛,老牛拉着沉重的石磙,石磙碾压在厚厚的稻秸上。“吱扭吱扭”的声音从石磙的木框边挤出来,父亲嘴里不住吆喝:“喝,喝,走好,走好……”老牛像听懂话似的,跟着父亲一圈一圈转,一遍一遍的碾压。母亲拿着木叉,不时地翻挑压过的稻秸,稻谷脱落干净,稻秸挑到一边,谷场上只有黄澄澄的稻谷,金黄金黄的,小山一样。性急的母亲,舀上一瓢,回家搓去外壳,做成喷香的白米饭,村子里就洋溢着米饭的清香。这是辛勤劳动的果实,是每个家庭的希望。
晚上,劳作了一天的村民们,坐在一座座小山一样的谷堆旁,边吃着晚饭,边聊着家长里短,农事天气。
天空高远洁净,月亮在云朵里穿行,宛如墨蓝色的幕帐上盛开着一朵银白色的莲花,阵阵晚风里,阵阵笑语欢声飘得很远很远。
如今,少时的农耕模式早已被现代化的机械设备所替代,然而,那些秋收的岁月却牢牢地刻在了心里,每每想起,总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