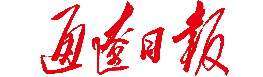●刘桂兰
年前归拢柜子里的旧物时,一捆毛线闯入了我的视线,尘封的记忆瞬间就被这团毛线轻轻勾动。我突发奇想决定重操旧业——为自己织一件毛衫。身为行动派的我,当下便翻找出四根织针。夜幕降临,灯光柔和,坐在沙发上,手指轻动,随着织针与毛线交织翻舞,恍惚间,又沉浸在早年的编织时光里。突然,一个念头如闪电般击中了我——我还欠父亲一双毛袜子呢!
年轻时,我是个编织能手。不管是毛衣毛裤、袜子、手套,还是款式精巧的贝雷帽、帅气的坦克帽都不在话下。什么元宝针、阿尔巴尼亚针、蜂窝针,这些复杂的针法在我指尖都能轻松驾驭。那时工资微薄,实在买不起现成的羊毛衫,一家人的穿着就全靠我这双手。母亲那件藏蓝色的精致开衫、公公那件实用的毛马甲、爱人的贴心毛背心、还有女儿的漂亮毛线大衣,无一不出自我手。妹妹家至今还保留着当年我给小外甥织的坦克帽,上面的每一针每一线都编织着岁月的温情。可如今回想起来,在所有至亲中竟唯独缺了父亲的一件编织品。
记得有一年冬天带着女儿回娘家,父亲看着外孙女脚上厚实的毛线袜子,目光里满是温和,轻声说道:“这袜子很暖和吧?”他只是随意一提,我也不过随口应了句:“等有时间给你也织一双。”那时的我怎么也想不到,这句轻飘飘的承诺竟成了我今生永远无法兑现的遗憾。
父亲出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命运的车轮自他幼年起便开始无情碾压他。双亲早逝,年幼的他和兄弟姐妹五人只能相依为命,尝尽了生活的酸涩。成年后怀着满腔热血毅然投身八路军,在战火纷飞中保家卫国。但生活的苦难在他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脉管炎。这病虽不致命却如附骨之蛆难以治愈,每到阴天下雨那钻心的疼痛便会如影随形,哪怕是炎炎夏日父亲的双脚也总是透着彻骨的寒意。
或许是以往的经历太过沉重,父亲的性格极为内向,不善言辞。家中的大事小情都由母亲拿主意。父亲在精明能干的母亲身旁,总显得有些笨拙,两人时常因为生活琐事拌嘴。但其实,慢性子的父亲有一双巧手,那些旁人眼中不起眼的活儿到了他手里都能化腐朽为神奇。小到柳条编的笊篱、筐篓,大到炕席、茓子,村里无人能及。每一道工序,他都做得一丝不苟,正是应了那句“慢工出巧匠”。
记得编茓子和炕席用的是高粱秸,制作篾子的过程繁琐又辛苦。先得仔细削去高粱秸的叶子并小心翼翼地劈成四瓣,再在水中浸泡两三天,等秸秆吸饱了水分变得柔韧才用刮刀轻轻刮掉里面的瓤。只有潮乎乎的篾子才好用,太干就容易断裂,稍不留意还会划伤手指。年复一年,每个冬天,父亲都在这冰冷潮湿的活儿里忙碌,腿疾也因此愈发严重。常常看到他在冬日的夜晚,默默地把腿伸到火盆边烤着那怎么也暖不热的双脚,脚上穿着厚厚的袜子,那是他抵御寒冷的最后防线……
眼下手中的毛线在织针间穿梭,每一针都像是在编织着往昔的回忆。如果父亲还在,我定会挑一个暖阳高照的午后,就像小时候他坐在屋檐下编筐篓那样,坐在他身旁为他细细地织一双袜子。用最柔软的毛线,织出最密实的针脚,让这双袜子包裹住他的双脚,给予长久的温暖。我还会边织边和他唠唠家常,讲讲这些年生活里的琐碎与美好,听听他那些藏在心底未曾说出口的故事。
透过吊顶灯散发出的一抹温柔,仿佛能看到当我把织好的袜子递到父亲手中时的情景:他那满是皱纹的脸上会绽放温暖的笑容,也会用粗糙的大手轻轻摩挲袜子,而眼中满是欣慰与感动。可这一切,终究只能在我的想象里无数遍的推演。我知道天堂里的父亲一定能感受到这份迟到多年的心意,也相信在另一个世界里他的双脚一定不再寒冷。
如今,我将对父亲绵延无尽的思念,细细密密地织进这尚未完工的毛衣里,每一针,每一线,都缠绕进美好的回忆与眷恋。
让这份深沉的爱在岁月里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