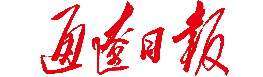●谭丽挪
太阳从楼顶探出圆脸时,晨雾便悄然退去了。不知是闷热的天气,还是胸中那股无名的烦躁,我竟鬼使神差地推门而出,恍惚间已站在汽车站前。“去乌拉盖啦!”的吆喝声像一根线,牵着我买票上车。
靠窗的座位映着晨光。玻璃窗上,我看见一个托腮的女人——她有着母亲的眼角,姥姥的唇纹。胸口隐隐作痛,这疼痛成了我最忠实的旅伴,在心室里敲着无人听懂的密码。
十年前离乡时,户籍档案上“山东”变成了“内蒙古”。少女时代像被突然剪断的风筝线,转眼间我已是个被柴米油盐腌入味的妇人。丈夫的领带、儿子的书包、影院里永远修不完的放映机,这些物件织成一张网,把我困在“妻子”“母亲”“老板”的标签里。
“可能是脑垂体瘤。”医生的话像块冰,顺着脊梁滑下去。诊断书在包里窸窣作响,像片枯萎的树叶。
草原是在我恍惚时突然闯进来的。布林泉的水珠溅在脸上时,我才惊觉已置身于《狼图腾》的梦境里。少年时代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见的草原,此刻正铺展在眼前:绿绒毯般的草甸上,野花像打翻的颜料盒;泉水叮咚,是大地在唱歌;几个牧童在水塘嬉戏,水花在阳光下碎成钻石。
天鹅湖像块被天神遗忘的镜子。野鸭带着雏鸟在波光里捉迷藏,它们的欢叫让我想起爷爷的狗尾巴草。那年邻家女孩抱着洋娃娃炫耀,爷爷用狗尾巴草编的猫咪,穗子一摇就活了。老人把草猫咪塞进我手里:“这草啊,给点阳光就疯长。”
湖水突然晃了一下。我掏出诊断书,雪白的纸张在阳光下透明得刺眼。撕碎的纸片像一群白鸽飞向湖心,水波轻轻一吻,它们便化作浮萍大小的舟。
回程的车上,我摸到包里有颗遗漏的纽扣——是儿子校服上掉的那颗。忽然想起今早出门前,丈夫默默往我保温杯里添了热水。这些琐碎的温暖,原来一直都在,像狗尾巴草籽粘在衣角上,跟着我走过千里万里。
草原的风追着汽车跑。后视镜里,我看见天空正把白云一朵朵种在乌拉盖的胸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