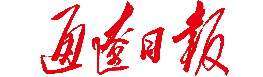编者按:
花开六月,踏歌而行。在这个美好而独特的月份里,我们为少年儿童准备了一份叫做精神食粮的大礼。这个月,我们与内蒙古作家协会共同邀约了全区儿童文学作家,在这里,用他们的妙笔和爱心描绘人生的美好蓝图,播种爱和希望的种子,引导和培养少年儿童善阅读、爱阅读的好习惯,以文学的力量,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根植向上向善的种子,以正能量的文学作品,精心呵护他们健康成长。
三岁的蝴蝶犬阿来随主人住在鲁北镇平房区一个胡同尽头。主人是一对盲人夫妇,年过花甲,膝下无儿女,靠政府救助为生。
胡同长约二百米,路面上布满坑洼,东接马路。雨季,路面积满污水,气味更差。在胡同北侧的水泥线杆上,探出一个铁皮伞,伞下吊着一盏灯泡。无论冬夏,天黑之前那盏灯都会悄然亮起,成为出现最早、离人间最近的一颗星。灯光照亮胡同,和路灯的灯光对接,直到被第二天的黎明淹没。有了这盏灯,在胡同里来往的夜行人再也没摔倒过,也没再丢过东西。
那盏灯是他们为了方便路人,请人安装的。住在整个胡同里的人都忘不了,此前的一个冬夜,邻居王师傅下夜班不慎摔倒被冻死,留下妻子和两个孩子。
住在盲人夫妇房后的是张大姐。张大姐单身,常来前院唠嗑,并带着瓜子、爆米花等小零食,话题多是抱怨在外地工作的一儿一女。
老两口理解她上班时每天忙忙碌碌,一时难以适应退休生活,劝她出去找点儿事做。张大姐也先后找过几份工作,不是嫌老板心黑,就是看不惯老板娘脸白,窝在家里更难受,最后干脆天天晚上来闲聊。
老夫妇得到政府救助,觉得应该回报社会,常去社区给孤寡老人义务做按摩。
阿来是盲人夫妇收养的流浪狗,它像个玩具,身上以白色为主,两只眼睛贴着大大的土黄色眼圈,像是小朋友画大熊猫没有画成功,画成了狗。盲人妻子定期为它洗澡,它浑身干干净净,跑起来像一个棉花团在地上滚来滚去。它也养成了良好生活习惯,定时定点如厕。
阿来成了他们的眼睛,邻居夸它“高手在民间”。附近的养狗人常牵着自家狗来学规矩。它在外面从来不对任何人呲牙,但是家里来了生人,就会立即警觉地站在主人身前,摆出保护主人的姿态。
张大姐曾被狗咬过,小腿上至今还留着疤,所以不喜欢狗。每次她来串门,阿来冲她摇尾巴,她就别过头假装看墙上的挂钟。
阿来也“玲珑剔透”,对张大姐也开始不冷不热。张大姐过分唠叨,它就会“哼”一声,迅速掉过头,用小尾巴“啪啪”拍地。
一次,张大姐说得激动,茶水泼到了阿来身上。它跳起来,冲张大姐吼一声,像是终于找到了吵上一架的理由。张大姐本来肚里有气,就下意识地举着茶碗冲阿来比划了一下。这下坏了,阿来马上跳起来提高分贝,拉长声音,连连抗议。
盲人妻子制止:“阿来,不许这样对待客人!”
阿来立即停止叫唤,看了一眼张大姐,眼神里似乎写着“算你运气好”,便转身默默去了墙角。
张大姐没料到弄巧成拙,讪笑着说:“个头不大,脾气比小老虎还大呢。”
阿来“哼”一声。
不过,阿来还是接纳了张大姐。主人不方便办的一些事情,全包在了张大姐身上。它虽然没做出示好动作,但眼神柔和了许多。
张大姐和阿来之间的感情升温始于一次闲谈。
盲人丈夫说:“这段时间我常在路上听到一个流浪犬的哀叫声,想将它领回家来。”
张大姐劝阻道:“还是别往回领了,一是街头流浪犬太多,收留不过来,二是若那只狗脾气不好,会欺负阿来的。”
蹲在地中间的阿来起身走到张大姐脚下,歪头蹲着,还伸舌头舔了舔她鞋上的尘土。张大姐心生温暖,表扬了它一句。它像是觉得被表扬是一件令人害羞的事,转身出去了。
从此,阿来对张大姐上了心。
一次,张大姐唠完嗑回家,起身猛了些,出门后眼前一黑,晃了几晃。送客的阿来见状立即追上来,低头轻轻咬住她的裤腿,领她慢慢往家走。快出院门时,一辆运煤车轰隆隆冲过来,阿来绷紧身子挡在她前面,直到运煤车走远,阿来才帮张大姐过了马路。张大姐示意它回家,它像是没听见,坚持要把她送到家。张大姐使劲儿地抚摸着它的后背,像和自己孩子说话“回去吧,我没事了”。阿来没有立即就走,蹲在地上冲着炕头“汪汪”两声,分明是说“别废话,赶紧躺下休息”。
第二天一早,盲人夫妇被阿来拽到张大姐家。
“是它非要我们来。”盲人丈夫笑着掏出艾草罐,“说是得给功臣按摩。”
张大姐鼻子一酸——她给儿女打电话总是不超过几句,儿女就都说“忙忙忙”挂了电话,现在却被一条小狗惦记着。
阿来见张大姐谈笑如常,看看主人,再看看太阳,抬头冲门外叫一声,意思是“既然没事,就别浪费时间啦,快出发去社区吧!”
岁月静好中的阿来想不到,一场灾难正在袭来。
一个冬夜,张大姐正纳闷胡同里的那盏灯怎么还没亮起时,阿来跑到她家,将她领到了医院。
医生告诉张大姐:“120师傅说是一辆中型货车撞倒了盲人夫妇,女主人当场死亡,男主人正在重症监护室里。”
护士对张大姐讲:“这只小狗跟着救护车跑了好几里路,没想到又找来了你,真是比人还有情有义啊!”
胡同黑了一夜,邻居都没睡踏实。
第二天,所有邻居都去医院探望盲人丈夫,还争着要陪床。有人发现,阿来在医院门口等了一宿。
天刚要黑,那盏灯又亮了,不知是谁打着的。
第三天早上,那盏灯刚灭,陪床邻居带回噩耗:盲人丈夫也去世了。所有在家的邻居都赶去殡仪馆为他们送行,敬老院组织召开了追悼会。
几天后,两个工作人员来找张大姐等邻居。一个人掏出一张印有盲文并盖着公章的遗嘱:房产和事故赔偿金百分之七十捐献给残联,百分之三十平分成三份,一份是那盏灯的电费,一份是阿来的生活费,一份是张大姐的报酬,由张大姐统一掌握。
张大姐的泪水落在遗嘱上,她找来电工,将那盏灯改接到了自己家,也成了阿来的新主人,决心好好照顾它。
那盏灯依然每晚照亮胡同,盲人夫妇的美德随着邻居的脚步走出胡同,传到了社会上。
一天早上,张大姐正靠在沙发上按摩颈椎,阿来突然撞开门冲着她喊叫,又上前叼住她的裤角往门外拽。张大姐恍然大悟:忘了关灯。她既自责,又感动,关了灯,抱起阿来请求原谅。阿来哼哼几声,舔一下她的手背,意思是:知错能改,可以原谅。
一个傍晚,张大姐出门溜达想到自己忘记开胡同里的灯时,心里一阵害怕,眼前立即出现了王大哥的惨状。她气喘吁吁地赶到胡同口,却惊讶地发现温暖的灯光已经洒满了整个胡同。
她进屋开灯一看,地下歪倒着一个塑料凳,阿来毛发蓬乱地趴在一旁,用埋怨的眼神望着自己。她这才想起来,盲人夫妇家一个开关安得特别低,原来是为方便阿来开关电灯的。自家开关太高,阿来够不到,它就从厨房弄来凳子,先蹦上去,再蹦起来按动了开关。从它的狼狈相上看,不知努力了多少次。张大姐心生惭愧,脸上发热,把阿来抱在怀里,摩挲着它的背毛连声道歉。
第二天一早,张大姐就找来电工,改低了开关。
不知道从哪一天起,张大姐发现自己不再发牢骚,浑身疼的毛病不治而愈了。
张大姐也当上了社区义工。黄昏时,常见她牵着阿来从胡同口赶回来。灯光依旧按时亮起,照起阿来脖间晃悠的红布条,像是跳动的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