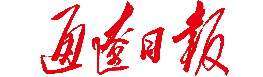□张淑清
故乡和城市就是一座桥的距离。石桥、木桥、断桥、长桥、短桥,桥中间住着一个或者几个月牙。
桥这边住过我的半生,我和一株谷子做朋友。我们在无数个带着露珠的清晨,在风中穿梭,奔跑。露水湿了我的鞋子和裤脚。谷子身上的香气,将我的每一根发丝熏染。很多人,不止我一个,有年老的二伯,青春懵懂的铁柱,还有一拐一拐走路的阿童木,发小桃花。像庄稼似的,生长在村庄的人,一群人,绕着一座一座山峦,一块一块田地,一条一条溪水,朝一个方向拥去——桥。
桥,多少年里沉默不语。一帮人在争论不休,一个说:过了桥,再走不远,就是灯红酒绿的城市,那里站着高楼大厦,车流湍急,那里遍地是商机,只要弯一弯腰,你就可以成为富人。不像在村子,种一辈子土地,也买不了城市的一个洗手间。一个说:过了桥,到城市后,大家能坐在门口的树荫下纳凉?捧着饭碗聚在石磨上,你吃我的,我吃你的?插秧,扬场,大事小情你在吗?一个说:你想要的城里怎么可以没有?如果城里没有,那就不叫城市。人们七嘴八舌,最后,有人嚎了一嗓子,别胡乱猜想,进城不就知道了?他第一个冲过桥梁,我清楚地看见,他左肩上搭件换洗衣服。跟在他后面的人,也不甘落后。城市像一个磁场,吸引着村子里的人。
在村庄和城市之间,父亲有说服力,父亲将农具一样一样挂在屋檐底,让它们在靠近自己最近的地方,一起看云卷云舒,日升月落。一起下地锄草、捉虫子、犁地、收割。很多时候,父亲与一根镢头,相互偎依坐在河岸,听流水一遍一遍发出潺潺的节奏,鱼儿在水中自由自在的游弋;大小不一的石头,以永恒的姿势跪在原地。望着一匹马过桥,没戴缰绳,马走在桥上时,顿了顿,扫一眼群山环绕的村子,想了想又回来了。
人和马大相径庭,人一旦选择离开,头也不回,恨不得一下子飞过桥。他们在过桥时,同父亲打招呼,你不走啊?在这里守着几亩地,有什么盼头?父亲摆摆手,仍在抽一支喇叭烟,烟草是父亲栽植的,不用去市场买。父亲有的是土地,烟叶子也泼实,指哪长哪,朴素真实。父亲盯着他们的背影,沉思很久,很久。父亲不明白,村子有什么不好?土地最靠谱,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房前屋后,点一棵南瓜籽,就是一棵苗,沿着石墙,柴禾垛,夏秋两季,结满南瓜。撒一颗玉米粒,钻出一株玉米苗,西风一吹,籽粒金黄。抛一缕秧,秋来,十里稻花香。谷物深入人心,喂养村庄,也养活城市。人说走就走,我时常看到,父亲咬着牙坚持,与他的草木不离不弃。父亲看着一个一个人过桥后,风物犹在,只是,出去的人,一年两年,十年没有回来。
父亲一边种着他的地,一边想走出去的人。那些人慢慢地被时间割去,仿佛一茬一茬收走的粮食。父亲有时经过他们住的房子,在一截黑乎乎的木头、一堵坍塌的墙、一扇摇摇欲坠的门窗、一片残缺的瓦前沿图索骥,找回一部分当年的烟火。父亲抚摸着老房子的墙壁、门楣,像和故人握手言欢。在一间屋子,一铺炕上,父亲曾与他们大碗喝酒,大口吃肉,说着荤话,谈论着各自的收成。父亲还和二伯掰过手腕,谁输了喝一瓢井水,谁赢了学猫叫三声。阿童木的家,也被岁月折腾得差点散架,喘着粗气,硬撑着立在一片土坝上,父亲蹲下身,在墙根,发现一粒黑亮的纽扣,一支别针,两个物什,全是当年阿童木在时,父亲帮着他拉犁留下的。草儿花儿在园子里野蛮生长,父亲摇摇头,笑了笑,走了。
父亲和走散的人,唯一的交流方式,便是常在对方寄居的宅院散散步,和那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说说心里话。
桥还是那座桥,河却瘦了,弱不禁风,宽阔的河面,裸露着褐色的骨骼,仅剩细长的一条线,河究竟遇到什么?大地知道,苍天知道,河憔悴的样子,令人辛酸。
父亲依在一棵杨树上,看着桥上的风景,一天比一天荒凉。出去的人,陆续有消息带回村子,有人在广场碰到二伯,他拎着一只空鸟笼,低着头似乎在寻找什么。那人喊了二伯的名字,二伯抬起头,警觉地问,你是谁?你认识我?二伯已经认不出村里的人。他拎着鸟笼,迅速折进人丛中。父亲的心,沉了一下,又一下。
父亲坐在河岸,看着一个个人去了彼岸,对他的儿女过河,在城市安营扎寨,不露声色,他早就预料,总有这么一夕,父亲在河的此岸,孩子在河的彼岸。他们不过是隔着一座桥,往返一回,像隔着万水千山。
我呢,在城市没有遇到熟悉的人。城市的路,千万条,蜘蛛网似的纵横交错,有一条通向我栖息的床。我有一张床就觉得很富有,比流浪的人和猫狗好一些。我和丢失村子的二伯们如出一辙,想回去又感到没脸见大伙。
我不止一次行走在繁华的大街上,对迎面过来的一头牛、几只羊深感亲切,它们看看我,我也看看对方。彼此在哪里见过,又在那里遗忘。牛羊进城,无非是消费城市。一条不归路,由不得它们。离开村子,我什么也不是。干着最底层的活,缅怀着远去的村落。
现在,贴我最近的路,就是二路公交车。我试图返回村庄,在返回之前,我要将身体内的尘埃,一路上的风花雪月,擦洗干净。向一棵沉默的稻穗,致敬。就连植物都清楚,村庄才是让灵魂纯粹干净的地方。
故乡,请等一等我的灵魂,不要让它吹着异乡的风,客死他乡。一场一场的风雨霜雪,令我遍体鳞伤。行走多年,我始终像走时一样,两手空空,一副干瘪的行囊。趁着我没完全老去,思维不混乱,把我接回故乡。我发誓,从此后,卸掉骨子里的欲望,返璞归真,清清爽爽,轻装返程。桥那端,我的父亲母亲,煲好我爱吃的饭菜,等我回到村庄。
故乡,请等一等我的灵魂。没有故乡,再繁华的人生也是流浪。余生,我学父亲,穷也罢,富也罢,与村庄生死相许,给灵魂一个永远的安放。
人回到村庄,我的灵魂为什么还在路上?有一个黄昏,枯藤老树昏鸦,我像父亲坐在桥边,看到一群人风尘仆仆从桥那头冲过来,他们奔跑的样子,如一匹匹马。最前面的那个人我看清了,他是阿童木,虽然他头上有了华发,额头皱纹很深,我不会记不住他。紧随其后的是桃花,我的发小。她和最初离家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眼睛眉毛下巴经过整容,原来的清纯荡然无存。最后那位是父亲牵挂的二伯,他老得不像样了,他一跑嘴巴上的白胡须就扬一下。我叫出几个人的姓名,他们没有搭理我,依然朝前奔跑。不一会儿,又出了村子。
我也拔腿就跑,想追上他们,被一块石头绊了一跤,坐起身,灵魂剧烈地疼痛。我捂着胸口,不知所措。这时,母亲原路呼唤我的小名:清儿,回家。循着声音发起的地方望去,炊烟袅袅,青山秀水白杨红瓦掩映处,那是我灵魂居住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