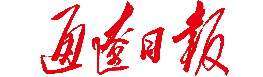□闫英学
顶针,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东北妇女普遍的家庭缝纫用品,通常由金属或牛角等塑料制成的环形指套,上面布满小坑,一般套在中指用来顶针尾,使手指更易发力,既不伤手指又能很快穿透衣物。
每当想起“顶针”,就会想起母亲的辛劳;每当想起母亲的顶针,就会想起儿时围坐在母亲身边,看着母亲一针一线为我们缝制衣裤、纳鞋底做鞋的一幕幕场景。
在懵懵懂懂的记忆中,六十年代中期全家随父亲下放。刚到乡下时,还没有通电,一到晚上小村便漆黑一片。
可是无论如何,全家四口人的穿衣、布鞋都要母亲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白天干不完的家务活,晚上天黑就要点上煤油灯,用那一点点的光亮,母亲戴上顶针,为全家缝制衣服。
漆黑的夜晚,小小的煤油灯光亮,真是难为了母亲。有时半夜醒来,发现母亲还在挑灯夜战,在灯光的影子下,母亲把做衣服的针放进头发里,反复摩擦几次,使针脚更加顺畅。
到乡下一年时间,村里也通电了。通电那天,只有少数几家准备了灯泡,好在母亲搬家时就有所准备,当晚灯火通明,引来一些村民观看。
村里有电了,母亲在白天干不完的家务活,晚上就可以在明亮的灯光下干了,缝制衣服的速度也快了许多。
日常生活中,经常看见母亲右手的中指上戴着顶针,当初是白色铁制的,后来又戴上了淡黄色牛角制的顶针。牛角顶针冬天用起来没有那样冰凉的感觉,而且当针的尾部顶上时,也没有铁器接触时的声响了。
有一年上中学,正是春天换季的季节,学校领导通知我代表学校参加县里举办的诗歌创作会议,母亲连夜为我赶制一件蓝色的布夹克,从当天买布到丈量尺寸,从下午开始到后半夜,母亲没有合眼休息,终于在后半夜为我赶制出合身的布夹克。夹克下面是紧身的,一边还有一个铁环,系带用于调整身形,煞是好看。
天亮时,母亲疲惫地用凉水洗洗脸,又为我们做了早饭,母亲让我穿上这件精心缝制的蓝色夹克,我看到母亲戴着顶针的手有些发红发肿时,鼻子便酸起来。
母亲不但会缝制衣服,还会裁剪,心灵手巧。村上一些妇女时常就来找母亲帮助她们裁剪衣服,样式美观,很受欢迎。
二十岁之前,穿过母亲缝制的无数双布鞋。穿在脚上,在外人看来,不但样式美观、大方,与商店里出售的布鞋没有什么两样,熟悉的人都为母亲的做工精细、双手灵巧而不住地赞叹。
七十年代后期,我当兵来到部队。母亲考虑我的汗脚很重,缝制了一双黑色灯芯绒布鞋,让父亲寄到部队,大大缓解了我常年穿部队军用胶鞋带来的苦恼。
母亲缝制的灯芯绒布鞋,在当时很时髦,褐色塑料底,用黑色迪卡布缝制两条压边线,很是精巧,鞋面上口用“五眼”压制,能系鞋带。穿在脚上,系紧鞋带很舒服。母亲还特意缝制了两双鞋垫放在黑色灯芯绒布鞋里。父亲寄来这双布鞋后,班里的战友都以为是在商店里买来的新鞋,不相信这是母亲亲手缝制的,纷纷夸奖母亲有一双巧手。
在部队期间,虽然没有机会天天穿布鞋,但在休息、上街时或出差便与军用胶鞋替换穿用。有时,躺在床铺上,一想到母亲缝制的那双灯芯绒布鞋,心里就暖暖的。
后来在部队生活中,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把母亲缝制的这双灯芯绒布鞋带到那里,从未离开过。只要是这双布鞋在身边,就感受到母亲的温暖,就会感觉周身热血沸腾;穿上这双布鞋,就会感觉到脚步踏实,故乡就在身边,亲人就在眼前。
在部队里,经常穿着母亲缝制的灯芯绒布鞋,两只塑料鞋底已经出现了“跑偏”,鞋面也灰旧了,鞋帮渐渐开始老化,布面与鞋底接触的两道亚纹也有些模糊。在结束部队生活前,只好不情愿地舍弃在营房里。
岁月沧桑,年轮更替。在不知不觉中,四十多年过去了,唯有母亲的顶针还深深刻印在记忆的深处。
小小的顶针,跟随了母亲几十年,是母亲的顶针“顶”出了我们的幸福,“顶”出了我们的快乐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