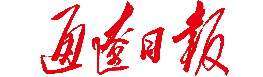□亚中跃
低矮破旧的平房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风霜雨雪侵蚀后巍然屹立。在秋季的夕阳落照中,小院的荒草和瓦砾夹杂在一起显得更加零乱。这幅图景,或许就是我早年在中学历史课本中读到的“废墟”。我伫立在院子里,凭吊这人去楼空的落寞小院,心里抑制不住涌出许多心酸。
这是我的家。严格说来,这是父母的家,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父母的财产。父母健在的时候,就长期居住在这里。院子并不大,从窗下量开去,到大门口也不过十一二米,况且大门口还盖着两间夏屋,一间装着父母多年积攒的旧物,另一间则装了半屋子的煤。夏屋里存放的铁丝、麻袋、废弃的煤油炉、旧纸盒箱子一类的东西,我看着就讨厌,不但碍事,而且上边落满了灰尘和蜘蛛网。每当父母让我到夏屋翻找点东西时,我便很长时间也无法找到,因此还挨父母训斥,抵触的情绪油然而生。有一次,我以帮助父母搞卫生的借口把这些破烂东西全部扔了出去。可是,我亲眼看到母亲迈着蹒跚的步子走到大道边垃圾坑前把那些东西又捡了回来。
父亲是一名共产党员,同时也是奈曼火车站货运主任。货运主任是个实权人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地方各企业和私企大宗货物主要靠铁路运输。当时车皮紧张,货主能请下一个车皮非常不容易。“铁老大”的绰号就是那个年代叫出来的。父亲在那时恰好在铁路运输的主要岗位上。货主每天围着父亲转,说如果请一个车皮,就给父亲五千元。可是父亲十分淡然,一点都不为之所动。气得有些货主背地里大骂父亲不懂人情世故,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人情味。父亲偶尔听别人转述,哈哈大笑,笑完后,脸色变得相当严肃,说:“现在有些人,当了干部,入了党,却没有一点共产党员的味道”。
“共产党员的味道”,也许这才是父亲骨子里的红色基因和毕生追求。
我和父亲也是常常会闹翻的。我觉得父亲实在有点过分。
我在铁路小学当老师的时候,还是八十年代初。几年后铁路分房子了,房子虽然简陋些,但是那年代有房子住,已经不容易了。分房后自然会盖个门房,总要装点杂物吧。我们的工资收入当时只有六七十块钱,两口子加一起月收入不足二百元。盖个房,少说也要几千块钱。我想到了父亲,我不敢开口,就撺掇妻子和我一起去找父亲大人帮忙。父亲想了想说:“这个忙我帮不了,沙子、水泥、砖、檩子、工钱,太多了,我找谁去呀,你们自己想办法吧。”父亲说完,不再吭声,屋子里的气氛尴尬到极点。我强压住心中的怒火,平静地对妻子说,咱们走吧。于是,我们走出父亲的家门……
我开始了大白天到处游逛捡砖头的生活。谁家盖房子拆掉的半拉砖,只要人家给,我就要。足足有一个多月,盖门房的材料准备得差不多了,就自己动手盖房子。我一个帮手都没找,画线、摆砖、和水泥、砌墙。下班后或是星期天,我一个人扛起了一项伟大的盖房工程。一天中午,我实在太累了,不管脏不脏,躺在地上就睡着了。不一会,我被人扒拉醒了,睁开眼睛一看,是父亲。我愣愣地看着父亲,不知为什么,我的泪水一下子涌出眼眶。父亲静静地看着我,半晌没说一句话,他叹了一口气,说:“我帮你们吧,小时候我没少干这些活……”父亲拿起地上的铲子蹲下来开始砌墙。
父亲常说:“自己的日子自己过,不要指望别人。”
父亲好像不是这个时代的人,一点也不随潮流。
一天,有个货主找到父亲,说有一百多只羊要卖到南方去。羊已经赶来了,圈在站前一个破旧的大院里。父亲查看了一下运输计划,说:“这羊走不了,没计划,没车皮。”货主瞬间涨红了脸,急得说话声音都有些颤抖了:“亚主任,你可要帮我呀,我是从各地收来的羊,我连草料都没有准备呀,这羊要是走不了,损失可就大了……”父亲说:“别着急,我给你想想办法。”货主从兜里掏出大约二万块钱来,趁着跟前没人,塞给了父亲,父亲非常生气地制止了他,并严肃地说:“收起来,我这个人从来不搞这一套,你不了解我。”说完,硬是让货主把钱收了回去。父亲拿起电话,马上找分局计划部门联系,分局又找沈阳铁路局计划科变更计划,为这位货主特别配备两辆敞车,第二天下午就把羊装走了。
过年过节,万家团圆。追求幸福生活是人们的美好向往,可是我们家过节,往往都有些与众不同。
大家坐在一起,酒过三巡,父亲又开始讲述他过去的故事。“我从小就没了父亲,和你奶奶下地干农活。晚上,坐在小板凳上看你奶奶纺线。你奶奶可以不点油灯,摸着黑纺线,一点都不打疙瘩。第二天起早三点多钟我就跟着你奶奶,用驴驮上纺好的线到北票县城去卖。那时候,山区有狼,我和你奶奶还碰上过一次,那狼就蹲在大山道上,眼睛发着绿光,我的心怦怦跳,你奶奶说,你个挨刀的,我们娘俩孤苦伶仃的,要吃你就吃吧,也不怕雷劈了你。那狼似乎听懂了人话,呆了一会,转身向远处跑去了……”
父亲讲的往事,好像传奇故事。
“你们现在生活好了,有的还当了官,有的入了党,你们要好自为之,不能捞钱。这辈子我没少经历各种运动,冻不着饿不着就行了,别把自己弄到监狱里去,到那时,妻离子散,家败人亡。你们可都是党员、干部……”
父亲的话重千金,字字砸进我们的心中,融化进我们的血液,并在我们的思想和灵魂里,种下了红色基因。
“谁让咱们是党员,是干部。党员就要有个党员的样子,干部就要有个干部的样子。”开会的时候,父亲经常这样讲。
父亲离开我们几年了。去世前,他把儿女叫到医院病床前,告诉我们说,他一生并没有什么遗产,只留下自己住的一个铁路平房,价值也不过几万元。
我们没有把房子卖掉,我偶尔会回去看看,站在小院子里想想过去的事。“党员就应该有党员的样子……”
这就是父亲留给我们的全部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