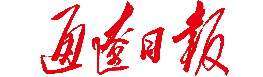●李洪彬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不久,日本从沈阳疯狂地西进,于1933年3月入侵了开鲁。日本侵略者在开鲁实现了军事占领、政治统治以后,接着实行了经济控制,从此开鲁各族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日军对开鲁长达 13 年的经济统治,绝非单纯的资源掠夺,而是一套从金融垄断、商业操控到毒品奴役、苛税盘剥的 “全方位殖民压榨体系”,每一项都浸透着开鲁各族人民的血泪,每一个数据都揭露着侵略者的贪婪与残暴。
诡秘的日本商人
早在中华民国时期,宫本岩寺和田茂七二两个日本人,带着家眷来到了开鲁,他们声称是做买卖的商人,就在此地开了个商号叫“三兴泰”。日本人在此地做买卖这件事,于民国十八年五月,被热河省民政观察员王枢视为“不是通商口岸”、以“究竟日人居住经营商业是否合于约章?”的问题,向热河省民政厅提出了疑问。而日本人闻之后,则以“民国四年五月《北京条约》第四条所载的‘如有日本臣民及中国人在内蒙东部合办农业及附随性工业时,中国政府可允准之’为有效,对于在东蒙有特殊权利”为理由,坚持其活动。因此,由热河省民政厅长邴某某署名,外交部交涉员裴子晏签名,申请外交部,内称“日本人在开鲁开商号,已经三、四年时间,是否合乎约章?……敝厅无稽可查,且案交涉,系属贵署(指外交部)主管。”而外交部则以“对外交涉应归中央管理”等因转请,此案终因上下推诿,未知如何了结。按理日本人在国外设立的商号,只做买卖而已,但他们却还测量气温、试验种植,调查满蒙内地商务的隆替及需要日货等各项重大事务。试问,几个离本国国土迢迢千里,浩浩重洋的日本人,为何对异国无垠的草原、偏僻农村小镇,如此感起兴趣来呢?
一份在伪康德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伪兴安西省调查员绪方笃太郎(日本人)在调查“开鲁经济情况”的一份报告中,暴露了部分答案。报告书中写道:“开鲁位于兴安西省东部(当时的兴安西省省会设于大板)是连接东、西扎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的纽带,是内蒙古贸易上的一个大门,是从内蒙东部区到内蒙西部区的一个桥梁。这样在满蒙文化交往位置关系上,它的经济组织一般是有其独特的性质”。一语道破了开鲁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什么“独特性质”?无非是日本侵略者阴谋以开鲁作为跳板,进而向内蒙东部进行军事侵略,经济掠夺,文化同化的狼子野心。
日寇侵占开鲁后,于伪大同二年四月在开鲁建立了伪兴安西分省;伪康德元年二月又把伪兴安西分省改为伪兴安西省;同时把兴安西省省会(当时省公署)从大板迁移至开鲁。开鲁县的地理位置在战略上的重要性。部分的证明了日本人宫本、田茂在日寇入侵东北前夜,以贸易为名,对开鲁进行了所谓“调查”的阴险目的。
日本人通过金融、商业吮吸开鲁人民血汗
清光绪三十四年新置的开鲁县,日本人占领后,为了加速他们殖民统治的步伐,急忙调来技术人员,对地域、人口、物产、风土、水源、地质等进行全面测量和调查。
开鲁镇内工商业(大户)有酒厂(利开号、万合永、隆兴号、兴隆皋)四家;有粮米加工业(磨房)35户,大户为:公兴厚、隆兴玉、同兴和、万合永、德兴号、大兴永、仁义永、顺发合、德兴永、增盛合等10家。还有布庄杂货铺等。总之,开鲁县农业牧业产品及土特产品资源雄厚,镇内工业商业户星罗棋布,生意兴隆,工商业发展前景可观。日寇对此垂涎欲滴,欲想一口吞之,所以千方百计地实行蚕食政策。
日寇侵占开鲁后,为了镇压人民,掠夺财富,驻伪兴安西省的日伪军有:日本军开鲁独立守备队、蒙古军开鲁第二警务军、日本宪兵队、移动保安队等。伪县政府还设置警察署、警务科,在城内四门及中街十字路口各设有派出所,担负所谓“治安”任务。日寇为了控制和搜刮开鲁人民的财富,从政界、军界渗入到商界。他们强行占据商务会的领导地位。
据满洲《每日新闻》昭和十八年在满洲年鉴《全满商工会一览》一文中登载就很显然;开鲁商务会会长牛国兴、副会长佐藤一夫、杜玉贵,常务理事铃木富雄。虽然他们是副会长、商务会理事,但商务会的事务都得他们说了算。日伪在开鲁县实行交出荷粮、皮毛统制、布匹、火油、火柴配给制措施,部分是通过商务会为其宣传晓喻各商户的。如有的商户违犯,就冠以损害了大满洲国利益的罪名(实际是影响了日本的掠夺和收集军用物资的任务)对所谓“经济犯”或灌辣椒水,或行刑拷打,以致关进牢房。佐藤铃木等人,是通过掌握的商业活动情况,发现所谓“经济犯”人的,他们从经济活动线上祸害开鲁老百姓。
搞垮了兴业银行。 民国时期,兴业银行已存储、兑换天津票、奉天大洋、银子、铜子、制钱、大洋等货币,沟通金融流通为其主要业务。对开鲁地区各种货币金融流通,和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日本侵占开鲁后,日本驻军大量的使用所谓日本纸币“金票”购买实物,并以大量“金票”换取开鲁当时流通的银子、大洋、铜子、制钱的硬通币。而当时流通的天津票、奉天大洋票被贬值,不仅使开鲁各族各界人民深受其害,兴业银行也在经济上受到了极大的损失,而且也失去了它在开鲁金融流通中的枢纽作用。
日本人为了全面占领开鲁金融市场,于大同三年1月3日,伪满中央银行开鲁办事处成立,9月28日发行纸币88170元。9月30日以现金购买日本“金票”(纸币)额达9635元;当时蓝面布每尺价一角二分,棉花每斤五角,高粱米每斤二分。换算一下证明,日寇用一把废纸就能买高粱米487150斤或能买棉花19270斤或蓝宽面布80020尺。而奉天大洋票、天津票先是被贬值,而后变为了不流通,烂在了开鲁民众手中。日本强盗以日本纸币(金票)换走了各种物资、银子、大洋、铜子、制钱等硬币的价值是无法计算的。
日本人搞所谓商业投资,实行高利盘剥。日本侵占开鲁后,除在五区(现麦新镇)抢占土地,成立稻子把,在三区成立平岗,天拜公司占地屯垦,在城外东西郊成立大烟组合外,还在商业上进行投资,仅康德二年就有25000元之多,主要是经营当铺,收购开鲁县的特产甘草和经营日本出口估衣等商业活动。日本人越发荣松办的兴隆当,有资金5000元,康德二年八月交易额当进1421件,赎出1158件,月末所得计10756元,纯利是资本金的二倍多;日本人富田开办的日升当,资金12000元。当进数为2118件,赎出1350件,所得利金为15016元,纯利是资本金的126.8%之多。日本当铺美其名曰押物贷款。它规定5元以上的利息为百分之八,50元以上的利息为百分之十,六个月到期后不赎,由当铺开卖,以当物时价低,卖时价高而获取了巨额利润。
抢购土特产品,牟取暴利。黑瓜子和甘草为开鲁特产。他们除收购黑瓜子运往当时的奉天(沈阳)外,特别感兴趣的是抢购甘草。开鲁所产甘草和东北满沟(俗名甘草沟)的产品齐名,因而开鲁甘草,在民国时期,中外驰名,历年都大量采挖,销往国内外。伪康德元年五至十月,全县甘草收购总量就达473800斤,在镇内有5家商户经营甘草。在5户商店中,就有两户日商,仅日商日光银行(资金1000元,代理人郭信久)就收购了20万斤。该年干品甘草价格上等每百斤为15元,中等为12元,下等为10元。而日商多以湿草论价,上等11元,中等9元,下等7元。随意压等压价(以干当湿,以好说次)来欺骗农牧民。每百斤少付农牧民3-4元不等,以每百斤平均少付3元5角计算,20万斤少付给农民7000元。为了垄断开鲁县特产甘草的收购,以日商为后盾的永和甘草公司(代理人施义九)又投资10000元,参加了收购竞争,日商以低廉的价格收购后,运回本国大板加工成酱油添加剂或其它副食品着色剂销往西方各国,牟取高额利润。
种植罂粟,贩卖鸦片,毒害开鲁人民。日伪在开鲁镇的城东南和西南郊区设立了大烟组合各一处,种植罂粟,收割的产品经过加工成鸦片。日本人就据为专利品,1933年3月,日军侵占开鲁后,为了毒害中国人民,搜刮钱财买军火,取缔了私人烟馆。开设了日本人的“日中天”“凌云阁”等97处烟馆。让吸毒者凭《鸦片瘾者领烟证》领取大烟泡在烟馆吸食。1932-1933年,日军侵占开鲁后,开大烟馆的是日本人,不仅图财害命,还有其政治目的。据老年人讲:那时的大烟馆有单间。门上挂个半截白布帘,两人一室,炕上有炕席。两边铺有罩着白布单的条毡,还备有两个方顶长枕头。两边条毡的中间是小炕桌,桌上放着铜盘、铜灯、烟枪等吸毒用具。在大烟馆凭领烟证每个大烟泡为一角七八分钱,私买得一元钱。当时一角钱能买10多个“大麻花”,一般人抽不起大烟,抽大烟的是伪满官吏、地主资本家等有钱人。有钱有势的人,为了摆阔气,吸毒时还要吃糕点、水果,高兴了把饭馆的饭菜叫到大烟馆来吃。大烟馆里吞气吐雾,狗苟蝇营,也是伪官吏、土豪们肮脏交易的罪恶场所,为投其所好,有时在大烟馆里找妓女喝花酒。
抽大烟的人也分三六九等,一个烟泡能抽10次,一等抽烟的也就抽六、七次就不抽了,二等抽烟的抽一等抽烟抽剩下的烟,三等抽烟的买二等抽烟的烟枪灰,过滤后,把烟汁往胳膊上扎(即扎大烟的)过瘾。所以人们说“大烟鬼,没脸鬼,扎到后来喝凉水”。许多吸毒者因为吸毒成瘾,面黄肌瘦,骨瘦如柴,整天泡在烟馆里,失去了劳动能力。就是家里有房有地有积蓄的体面人,也经不起长靠久耗的吸毒之患。到后来倾家荡产有之,卖儿卖女卖老婆的有之,当小偷做乞丐的有之,披麻袋片蹲阳沟,冻饿致死,无人认领的有之。据统计:仅镇内97处烟馆,年交易额为123595元。可买高粱米6179750斤。一年吸毒消耗可供五口之家食用300多年。日寇经营种植、贩卖鸦片,不仅大量消耗了开鲁人民的财力,更为严重的是腐蚀了一部分开鲁人民的肌体。
其罪恶目的是使中国人民通过吸毒成为“东亚病夫”而无力反抗其残酷压迫,在政治、军事上达到其长期占领的险恶目的。
利用捐税途径,大量搜刮民脂民膏。日伪于康德元年在开鲁成立了税捐局。当时,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百姓生活如牛负重,苦不堪言。所谓苛捐杂税,苛到地方税有26种,什么田捐、车捐、粮捐、牲畜捐、甘草捐、瓜子捐、婚书捐、妓捐、羊猪小肠捐,无捐不有;杂到国税多达25种,什么田赋、契税、屠宰税、粮石税、斗用税、酒税、烟税、皮毛税、印花税、无税不收。那时,干税收员这一行是肥缺美差。没有在公家干事的硬门子介绍,是当不上税收员的。伪满的税收员不是某某科长的兄弟,就是某某厅长的小舅子,那时税收员所到之处,只要把手一伸,二话不说,对不起,掏钱!当年的税捐局,没有完善合理的税务制度,加之管理混乱,把关不严,收多收少全凭税收员之口。收多了你也讲不出理去,弄僵了给你扣个“抗税不交”的罪名,送你去蹲笆篱子,正因为如此,税收员登门,如阎王爷造访。纳税人只得笑脸相迎,小心伺候。收税员吆五喝六,吹胡子瞪眼,狐假虎威。
从伪兴安西省调查科至开鲁的日本人绪方笃太郎,在伪康德二年10月25日上报给兴安西省政府的调查材料中看到,日伪为向开鲁人民征税,干出了多少卑鄙可耻的勾当。如为了征税在康德二年10月25日把开鲁商户统计为432户。为什么经过日寇的侵略和掠夺,开鲁商户不但没少,怎么反而多了起来呢?原来他们为了搜刮民财竟把妓院8户、大烟馆97户,拎鞭的牛马经纪人5户,也统计在商户内了。实际上是322户,资金是368180元。一年交际额为3903000.元,所得纯利为224000元。这已经是调查完的发生额了。值得注意的是,日伪还考虑商人上税怕过多,可能上报的数字少,也得照数字要增加10%-20%的税金,这不仅增加了商户的支出,而且也增加了消费者负担,对于收购土特产品的税率,高得使人无法承受。如收购甘草,每百斤干湿均价为13元,而税金每百斤都另缴纳8元。税收总额占收购价的61.5%。伪康德元年5月——10月6个月的时间。收购甘草的税金,就达1137.12元。
利用所谓“储蓄”吸吮农牧民血汗钱。 伪康德七年,在农村牧区进行了所谓“国事调查”,农牧民称之为“估家底儿”。他们将土地、房屋、车辆、牲畜、农具等都估了价,定为“资产”而后按资产总值的比率,确定所谓“储蓄”额,由每屯设的储蓄员挨户收取,月月上交“兴农合作社”。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知其败局已定,催逼的更甚了,警察所,屯公所也出面助纣为虐,交不上者就冠以反日的罪名。
日本人恶行激起人民反抗
在这期间,伪满洲国颁布了《保安矫正法》《思想矫正法》,对于凡“认为有犯罪危险的人”和“可能有犯罪危险的人”,一律捕送矫正辅导院。可是,日本侵略者的这些“措施”并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更激起了当地群众的反抗情绪和斗争意志。1944年春,在开鲁县的双合兴镇(今麦新镇)就流传了一本由马鸣鸾老先生写的抗日《正大光明》书籍,作者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预言侵略者必败的下场,激励人民坚定信心,投身反抗侵略者的斗争中来。
孰不知,这本书很快就被双合兴警察署长肖恩和查获了。他如获至宝,亲自送往开鲁县警务科,邀功请赏,日本人严令追查。马鸣鸾及其儿子马海楼、双合兴清真寺阿訇石克元、广增永糕点铺的刘殿增、大烟馆的宋文彬先后被逮捕、关押、用刑。日本警官大井亲自审讯马鸣鸾,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马鸣鸾挺身而出,承认该书是他写的。大井厉声大喝:“你是不是共产党?”“我知道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救星,可惜没见过”,马鸣鸾从容对答,毫无惧色。“这书是谁让你写的?”“是我的老祖宗钟馗让我写的。”“钟馗什么的干活?”“钟馗是打鬼的法师,哪里有鬼都打,一个不留,都打下地狱……”没等马鸣鸾说完,大井爆跳如雷,“巴嘎、巴嘎”破口大骂,顺手抄起茶杯向马鸣鸾砸去,马鸣鸾没有被大井的淫威吓住,老不示弱,“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捡起身边的炉盖子,照大井打去。大井一闪身,身后的穿衣镜被打的粉碎。对抗的结果,当然是马鸣鸾遭受了更多的皮肉之苦,坐了老虎凳、灌辣椒水、吊打……
体无完肤的马鸣鸾始终没有屈服,表现出了一个中国人宁死不屈的铮铮铁骨,也点燃了民众反抗的火种。
这段历史,不仅是开鲁人民的血泪史,更是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抗争史。它深刻警示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软弱必遭欺凌;唯有铭记国耻、砥砺前行,才能守护先辈用鲜血换来的和平,才能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它如同一本厚重的教科书,让每一个中国人在回望苦难时,更坚定守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决心,在传承抗争精神中,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