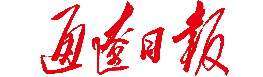母亲安志英被送人时还不足八个月。她被王氏从已死去多时的姥姥身边抱起时,瘦得像一只小猫崽,连大声哭叫的力气都没有了。从此母亲改名叫王丫。她到老王家以后,养母连续生了两女一男,这三个孩子成了母亲在这世间为数不多的亲人。
十八岁,母亲成了新嫁娘,新郎一表人才——即便在三十几年后我用苛刻的目光打量这个男人,仍能依稀看得出他当年的英姿。说来比较有意思,有一天这个叫王俊青的男人去我们村卖豆腐,毛驴车停在我家门前不走,叫卖不休。当时父亲也在家,便和母亲出门去看,我们也都跑出来凑热闹。母亲刚到院门口就停住了脚步,用极低地声音告诉父亲,这个人好像是王俊青。
“是谁?”父亲的声音异忽寻常的大。
那个男人开始说话了。
“我是王俊青,到你们村卖豆腐。路过你们家,就想顺便看看。”他显然有点底气不足,声音软塌塌的。
“欢迎欢迎!到屋里坐坐。”父亲竟如见到多年老友般热情,他不仅递上香烟,还让我们叫这个人“王叔”。王叔羡慕的目光从大姐身上挪到弟弟身上,又从弟弟身上移到我和妹妹身上。
“孩子们长得都好!好!真是水灵……老儿子都这么大了!”
我们都感觉出了他语气里的酸涩。母亲没说什么,但是她的脸上毫不掩饰地露出了一种满足。在这件事情上,我的父母表现出了少有的默契。据说这个男人回家后就病倒了,没过两年便郁郁而终。
我无意窥探母亲的第一次婚姻,这似乎也成了我们姐弟几个的禁忌。然而,从曾经的只言片语中我还是明白了母亲初婚失败的原因。王叔由寡母养大,母子相依为命。然而新妇入门之后,老太太发现儿子的爱竟然瞬间转移给了别人,于是对我母亲百般虐待。甚至在母亲即将生孩子的时候,还让母亲下地干活。加上没能生儿子,婆婆的打骂升了级,偏偏做儿子的孝顺,性格懦弱,无法呵护妻子。母亲性子刚烈,不堪其辱,遂离婚。但是母亲没有料到的是,婆婆竟找人打理官司,把孩子留下了。母亲在回到姥姥家后想女儿想得发疯。黑天白日往大坝上跑,见到小孩子就嚎啕大哭,寻死觅活。姥姥无力照料母亲,这时母亲的姑姑心疼侄女,当起了媒人。母亲明白自己是一个累赘,什么都没说便再一次草草嫁了人。
但是父亲治好了母亲的“疯病”。父亲会说书、会唱戏,农活做得好,在西花村里扭秧歌是打头的。
但是,为什么父母总是吵架?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很少在家。偶尔回家,他们也是吵架或撕打居多,害得我们四个孩子担惊受怕。所以,我们宁愿父亲不回家,母亲领着我们过日子就挺好。
印象最深的就是母亲给我们洗澡。每到夏天的黄昏,母亲就把晒好的一大盆水端到屋里,放到一个凳子上,我们挨个儿进盆里洗澡。我最喜欢母亲用水瓢舀着热乎乎的水浇到我头顶上的感觉,麻酥酥的,又有点痒,母亲用手挠着我的头,我用手去捂住眼睛,阻挡住水流,很是欢乐。母亲把我们一个接一个地洗完,用毯子一个一个地包好,就清理地上的水。我们四个围坐在毯子里,一字排开,只露出小脑袋,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还不时地故意挨挤着你撞我一下,我撞你一下,那个小屋里充满了笑声。
母亲是个讲故事的高手。有些故事常让我们失声尖叫,这时大家便都挤进母亲的被窝,纷纷抱住母亲的胳膊和大腿,连大气都不敢喘。有一次,母亲讲到一个爱情故事,说“因一个男的‘吐痰机敏’,女的就相中他了。”我们全都没听懂。
“妈,什么叫‘吐痰机敏’?”我们几个异口同声了。
母亲吱唔半天,“‘吐痰机敏’好像就是吐痰吐得高,吐得远吧。”
“啊?”我们都张大了嘴巴。这是什么缘故啊?吐痰吐得高,吐得远,美丽的女孩子就被打动了?
接下来的好一段时间,我们姐妹几个都玩起了一个把戏,比赛着吐痰,看谁能吐得又高又远——这件事成了多年后家庭聚会时最让人倾倒的笑话。
即使在最贫困的日子里,母亲也没能放弃让我们读书的打算。在这一点上,父母达到了惊人的一致,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读书。我家家徒四壁,却有满满一木箱的小人书。《苦儿流浪记》《三毛流浪记》《三打白骨精》……一个又一个神奇而美丽的故事,让我们的童年不再贫瘠。记得有一次我生病,需要每天到镇上的医院去打针,只能住在姥姥家。母亲走了十来里路来看我,她给我带来了一本小人书《悲惨世界》。这本小人书陪我度过了那痛苦而寂寞的卧床时光。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母亲给我订了报纸,上面连载着《大人国和小人国的故事》。我对文学的喜爱大概就是从这一个又一个故事、一本又一本小人书开始的。
母亲还会唱戏。《猪八戒拱地》《梁赛金擀面》等戏曲我们姐妹均能成本大套地演唱。受母亲的熏陶,我们姐妹几个都热爱文艺。听评书、唱拉场戏、跟着电影放映员把附近的村子跑个遍,母亲都极力支持。我们还常常自编自演,把头发梳成高高竖起的发髻来扮演八仙,晚上披着床单在篝火的烟雾中飘来飘去扮演仙女。于是,那个小院又充满了快乐的笑声。
但是童年的记忆中,也充斥着数不清的烦恼。冬天的时候,我们常常一病病一炕,一个哭都跟着哭。母亲哄好了这个,再抱抱那个,最后自己也常常落了泪。那个寒冷的小屋,四面漏风。母亲用纸糊住了窗户缝,用塑料布在玻璃窗户里外蒙了两层,还是不顶用。睡觉的时候,我们都不敢脱棉袄棉裤,母亲也不敢给我们洗澡。后来,我们几个身上都生了虱子,痒得我们睡不好觉,四处乱挠。于是,母亲在朦胧的灯下给我们捉虱子的身影就印在了记忆深处。
好不容易熬过冬天,来到雨季,麻烦却更大了。常常是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母亲把所有的盆盆罐罐都摆出来接雨水。有时,雨下得大,纸糊的棚都掉下来,母亲就把破塑料系在棚条上接水。晚上睡觉时我们东一个、西一个也完全躲不开,有时就相枕而卧。于是,雨水敲打盆盆罐罐的声音就如乐曲一样,又存进了童年的记忆里。
我们是多么希望有一个不漏雨不透风的家啊!终于,在我十岁的时候,我们搬到了村子中心,也有了一个新的家。
新家仍是两间土房。这次不漏雨了,但是随着我们的长大,它就变得太过于狭小。里屋一分两半,一铺炕占了一半面积,炕下靠西墙是一个老旧的乌七抹黑的八仙桌,紧挨着是父母结婚时的两个箱子,这两个暗红色、油漆斑驳的箱子由凳子支撑着,和八仙桌一边高。这就是我家仅有的家具。吃饭时我们把一个长方形的矮桌摆到炕上。外屋是南北两个大锅台,南面的给人用,北面的烧猪食。靠着北面锅台的是两个缸,一个装水,一个装猪食。剩下的空间就完全留给了烧火用的柴禾。
我一直不喜欢母亲把柴禾堆在屋子里。母亲的解释是,夏天雨水多,冬天有霜。总之,在记忆中,母亲并不是一个很会整理房间的人。
或者说,她是完全没有精力了。四个孩子,所有的衣服全靠她用手来缝,她还养了一群鸡和两只猪。忙完家里的活,又要去忙地里活儿。记事以后,我似乎就从来没有看见她睡过觉。我们睡觉时,她缝缝补补,洗洗涮涮;我们醒来时,她要么在做饭,要么就在园子里干活。
2004年,我们姐弟四人相中了镇里的一个房子。那是一个宽敞明亮的大院,四间大瓦房,松木檩,两间厢房。猪圈牛棚应有尽有不说,还有一个大园子。我们当即决定,不管怎么难都要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于是,我们果断地交了定金,接下来就是分头求借。在一周内,交齐了尾款。
签合同那天,我送走卖家,在每个屋里都转了转。站在院中,我打量着这个敞亮气派的院落,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感澎湃于胸让我热泪盈眶。
为了给父母一个惊喜,买房子一事我们一直瞒着父母。等我们把屋里屋外粉刷一新,换上新买的窗帘床单,我们姐弟几人迫不及待地雇好车去接父母。一路上我们想像着父母会说什么话,他们看到新居后会是怎样的兴奋。
母亲的的确确是被忽然从天而降的一个大房子给“砸到”了。她结结巴巴地问了半天,又跑出门外看到了来搬家的大车,才终于相信这是真的。仍记得母亲站在那个将属于她的大院前的表情。她近乎痴呆地凝望着那瓦房,用近乎呓语般的声音说:“这就是咱们的家了?”
母亲劳碌一生,清贫一生。两次婚姻,痛失长女,抚育四个子女成人。五十多年里,她一直在狭小逼仄的空间里生活着。她的手长满了老茧且处处开裂,她的脸上沟壑纵横。如今,她看着这忽然间飞来的房子,喜悦的泪水泉般涌出。
我抱住母亲,搀扶她走进了属于她的家,心里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当然,没过多久,父亲也被接来了。虽然他表面上装得有些生气的样子,但是他这儿摸一摸那儿瞧一瞧的样子还是引得我们偷笑。父亲变了。父亲几乎以让人震惊的速度在变化着,他先是果断戒了酒,接着又戒了烟。而且他忽然间没了脾气,特能忍耐母亲的唠叨指责。
在一次家庭聚餐时,父亲总结出了我家的两个“凡是”:“凡是你妈说的都是对的;凡是你妈说的都得去做。”我们哈哈大笑,母亲笑出了泪,用拳头去捶父亲。
母亲六十三岁时成了城里人——她得了哮喘,病得连一碗水都端不起,我决定把父母接到城里来住。刚搬到楼上,她指着旁边的次卧问,“这是谁家啊?”晚上看着街上亮闪闪的路灯,她既是喜欢又惋惜道:“这得浪费多少电啊!”
母亲没有如我们希望的那样去扭秧歌跳广场舞,她有更高的追求。她每天捧着本字典识字,写日记,还练起了毛笔字。前几年竟然和另一个老太太抬了一架二手电子琴回来。用父亲的话说便是“家里从此不得消停。”要么是未必悦耳的琴声绕梁——母亲跟着抖音学琴,一个谱能唱上八百遍;要么满床满茶几的红红绿绿的纸张——母亲的剪纸栩栩如生,窗子上、镜子上到处贴着母亲的大作。无论春夏秋冬,我家阳台上都姹紫嫣红——母亲把一朵朵形态各异的纸花插入花盆中,完全以假乱真。
难已置信,我的母亲今年已七十有三!看到她的孩子们都有了归宿,我的母亲也一天天地变化着。她不再动辄骂人了,不再唠叨往事了,不再唠叨父亲了,和她的姑爷们相处得也很是融洽。
母亲如今成了网瘾老太太。她不仅热衷于在所有看到的视频和文字下面发表评论,还热衷于转发各种小视频,甚至常常“晒幸福”——她在她的老头正拿着手机看二人转时偷拍下视频并小声说,“这是我老头,快八十了,拿着手机玩抖音呢!”或者在一桌菜摆上桌,大家刚要动筷子前大吼一声“都别动!”并拿着手机咔咔一通拍,然后发朋友圈。以前,每次给母亲买衣服都要被她一通暴骂。现在无论给她买什么她都乐颠颠地接过去,还要梳光头发让我拍照。这个母亲节,我给她在网上选衣服,结果一件粉红的和一件水蓝的衬衫她都相中了,委决不下。
“都买了吧。回来不喜欢的话再退。”我以为母亲会骂我败家子,没想到母亲大大方方地说,“行。如果两件都好就都留下。”
“本来只想给您买一件,结果您却故意选两件。啥时候变得心眼这么多呢?”我故意心疼钱的样子引得母亲笑出了泪。
岁月静好。这是此时我最为深切的体会。
愿母亲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