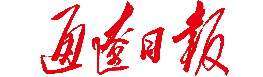□安艳学
一
时间如白驹过隙,一晃,高考到来,高中生活正式告一段落。我知道,检验自己努力成果的时候到了,我只有用心对待,方能问心无愧。紧张的考试过后,剩下的就是焦急的等待。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考入了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从小镇来到了城市,一切都令我感到新奇,尤令我欣喜的是在大学里,能够聆听教授们的谆谆教诲。
我们班有29人,班主任是年轻帅气的许光烈老师。许老师非常有才华,给我们教授现代汉语课。在毕业典礼上,他代表全院年轻教师发言,真是实至名归。
讲文学概论的李井发老师,有时讲到动情处,近乎声嘶力竭,一个个针砭时弊的文学批评案例,在我们的耳畔回响。从此,在我们的心底,埋下了文学不单单是西湖荡舟的美好,更是植根于现实生活有着极强生命力的种子。
在学习古代文学唐代部分时,我们遇到了刘永良老师。刘老师语气平和,写着一手飘逸的粉笔字。老师讲课时,出口唐诗,闭口唐诗,还不时秀一下戏曲,课堂上的古典风味浓极了。
有一天上外国文学课,只见一位五短身材、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年男人,步履矫健地走上讲台。他放下讲义,双手扶着讲桌开讲了,语速快,且含混不清。说实话,一节课下来,我一句完整的话都没有听明白,更谈不上记笔记了。
外国文学对中文系的学子来说,是必考科目。而老师的讲义又往往包含着重要的考试内容,因而上课时记笔记就显得尤为重要。课上没有记下来,那课下就得补,我只能借同学的笔记来抄。
一回生,二回熟,渐渐的我对教授的语言,也能听个一知半解,他的讲义也基本能记下来,虽然还不是很完整,但较之前已是很大的进步了。
慢慢的,我对教授其人,也略知一二。他叫孙宾,毕业于南京大学,是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用现在的时髦话说,我遇上“大咖”了。
我向来推崇“笨鸟先飞早入林”的道理,并常常身体力行。通常距离考试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开始着手准备。一有空闲就待在宿舍,撂下蚊帐啃书本、背笔记。在这样的努力下,考试顺利通过,一颗悬着的心也终于落了地。班里有三个人没及格,只能补考,其中一位还是个女同学,她得知消息后,哭得很是伤心。
师范院校的学生总得要实习。说来也巧,我们这个组的带队老师恰好是孙宾教授,实习地点是通辽市双泡子电厂子弟学校。
这天早上,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坐上了去电厂的通勤车。一上车,就有人与老师搭话:“孙教授,去电厂啊?”“是啊。”老师笑呵呵地答道。“有什么事儿,打个电话就行了,还要您亲自跑一趟!”“那哪儿行啊,这次是带学生去实习。”老师认真地说。“哦,有啥事儿,知乎一下。”“好的。”说着说着,车就到达了目的地。我们先到住宿的地方,安顿妥当后,又去了学校熟悉环境。一路走下来,也到了午饭时间,便来了电厂职工食堂就餐,这里的伙食真好。
我们的实习过得非常愉快且顺利,就连看电影都不用买票,说是老师的弟子就行;来回坐通勤车也是一样,我们实实在在享受了作为老师弟子的优厚待遇啊!
实习生活结束了,我的大学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
二
我刚到师院报完到,就被告知住宿的地方在五中,而且仅限男生。这于我们而言,倒也可以接受,毕竟不是太远,也就是几条街的路程。期限是半年,来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就会回来。
住在校外,相较之下,我们自由很多。只是冬天要麻烦些,天还没亮,就要从热乎乎的被窝里爬出来,洗漱完,来到学校食堂或校外的饭店,要上一碗抻面或是一根油条,外加一碗小米粥或豆浆。吃完早餐,马不停蹄地赶到教室,准备上课。
晚上9点半下晚自习,我们结伴走在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下,不时地有人闲情雅致地唱上一曲,别有一番情趣。
半年后,我们回到了校园。我的宿舍在二楼,头一次住楼房不太习惯,又因为胆小,只好住下铺。结果还是出了状况。第二天醒来时,人和被子都在地板上,原来是我在夜间打把式造成的,心里庆幸,多亏选择了下铺,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三
在师院的这几年里,学校食堂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以致于现在想起来都历历在目。
由于我们是上大课,通常情况下,上午11点半才放学。在这个节点上,到食堂打饭,也就只有馒头了。
一天一顿还好说,就怕是一天三顿,顿顿是馒头,最后,我一看到馒头,条件反射似的吐酸水。
这样的情况,就在我即将毕业时发生转机,久违的米饭与我见面了。为了打到米饭,再也不用绞尽脑汁的加塞,苦苦久等,从此望米饭兴叹的情况,一去不复返了。无论如何,总该是令人欢呼雀跃的事了。
时至今日,我时常会想起在师院读书时的青涩年华。那段难忘的大学时光,让我倍加珍视,受用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