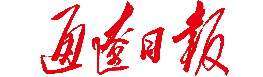□包永强
记忆里的冬天总带着炭火的暖,那暖意从岁月深处漫出来,至今仍萦绕在心头。儿时冬季农场的清晨,天幕还凝着霜,父亲的棉鞋已在土炕前踩出沙沙的响声。他把五个孩子的棉衣棉裤轻轻放在身边,摊开在火盆上逐一翻烤,动作轻盈而专注,像侍弄晒谷场上的稻穗般仔细翻转,父亲干瘪瘦弱的手掌被烤得通红。
我常常蜷在被窝里,静静地望着他的身影。那件棉袄前襟早已被岁月磨得发白发亮,他坐在马扎木凳上,用炉钩子拨弄炭块(苞米芯烧后而成的炭),火星子便顺着他低垂的额头往上窜,映得脸颊都红红的。等到棉衣烤得发烫,散发出温热的气息,他就把袖子捋顺,按从大到小的顺序,逐一为我们姊妹五人穿好。当我触到带着体温的衣领时,我总会咯咯笑起来,父亲便轻声哄道:“快套上,别冻感冒。”
在我儿时,他的饭食总潦草得叫人揪心。开饭时,他捧着小碗坐在圆桌炕沿上,快速地扒拉米饭,二三分钟父亲就能吃完一碗饭,他端着空碗去添饭,看见盆里的米饭所剩不多,他顿住,眼神中闪过一丝犹豫和不舍,喉结微微动了动,转身把空碗搁在桌上,说:“你们吃,我吃完了。”说完便出屋干活,越过门槛时,裤脚还沾着清晨烤火盆时落下的炭屑,那星星点点的黑色,像是时光留下的印记。
去年整理旧物,在仓房那布满蜘蛛网的角落里,发现那只火盆。铁锈早已无声息地爬满了盆沿,层层叠叠,诉说着岁月的沧桑,而盆中却不见一丝炭灰的踪影。我的指尖抚过凸凹纹路,仿佛在触摸一段沉睡的往事。忽然,某个雪天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大雪纷纷扬扬,天地间一片雪白,我的小手冻得通红,父亲捧住我的小手托在火盆上。原来有些温暖,早已顺着那跳动的炭火渗进血脉里,即便如今火盆早已冰冷,那些被烘得发烫的时光,依旧还在记忆深处轻轻冒烟,温暖着我。
父亲总是家里第一个起身,也总是最先一个放下碗筷,总是把最热的棉衣穿在我们身上,把最沉的担子扛在肩头,用他并不宽阔却无比坚实的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如今我才懂,那些没说出口的爱,都藏在冒热气的棉衣里,藏在空了的饭碗里,藏在他转身时消瘦单薄的背影里——这份深沉未曾说出口的爱,化作我生命里的春天,在记忆深处生根发芽,四季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