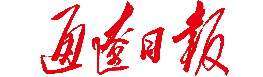□王玉全
多年以后,我经常想起过去的一幕场景,像电影一样在脑海中回放……
一团团牛群和马群溅起的烟尘刚刚散去,街口又响起了清脆的哨子声,一个小黑小子嘴里叼着哨子,腮帮子鼓起老高。
三通哨声过之后,他高高举起哗楞棒子,扯开嗓子迎风高喊:“松猪啦,松猪啦!——”听到这声音的妇女们急忙放下手里的活计,奔向猪圈门子。
圈里的猪一股脑地冲了出来,一会儿功夫,刚刚静下来的中心大街又沸腾起来。
村西头是一个天然的大水塘,猪群跟牛群、马群一样,趟过水塘才能达到放场。
猪群进入水塘,父亲一边辞别叮嘱的人群,一边挑起扁担,沿着水塘边跟在猪群后面。
村西北也有一个水塘,比村西头的要大得多,我们习惯叫它“北大坑”,春夏秋三季有水,冬季有冰;莫力庙水库的灌渠由南向北穿过村西的查干淖尔预备库,一个闸门的自然渠弯弯曲曲地通向村西的一片片稻田,猪放场就处在这条自然渠和北大坑之间的草地上。
父亲几年前做过开膛大手术,不能干重活,生产队安排他放猪。父亲大病初愈,不能跑动,我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猪倌儿。
春草发芽的四月,天气乍暖还寒,猪在这个季节主要吃野菜,苦麻菜、婆婆町、苍耳、红根儿等。
天气热了,父亲就用一根短木棍横向绑在电话线杆上,把长衫挂在木棍上,坐在阴凉下抽烟。
淘气的猪走远了,父亲就大声吆喝,猪根本不理他,反倒好像是在吆喝我,于是我便跨上长长的柳树条子,抖擞着哗楞棒子冲过去。
老艾奶奶家一口老母猪,一窝总能产十几个猪羔子,这头猪是我的重点看管对象,每到放场一个多点的功夫,它就带领着一群小猪羔子溜圈,一旦超出我追赶的距离,它便加快速度,两排大奶子几乎要挨着地了,在跑动中左右大幅度摇摆;它偶尔跑水路,偶尔跑旱路,一路越沟过岗,穿越树林;我手中的哗楞棒子一直在响,两条小短腿一直在奔跑,胯下的柳树条子摩擦着草丛和地面发出嗖嗖的响声。
当我满头大汗赶到老艾奶奶家门口的时候,老艾奶奶正在猪槽子边上,母猪和它的孩子们正在低头大口大口地吞食槽子里在泔水缸里浸泡过的苍耳叶子和嫩茎,槽子里的水面上漂浮着零星玉米糠麸。
每到夏季来临,农家园子里的蔬菜成熟了,老艾奶奶就在我追赶她家母猪的时候,把怀里用衣襟兜着的几颗鸡心柿子塞给我,并当着大家的面夸奖我是个好孩子。
牛吃青草了,牛粪也很薄;猪饥饿忙着找食物的时候,我会很无聊,就四处留意牛粪,趁屎壳郎还没来得及滚走,我就把它们反过来,让接触草和碱土地的那面朝上,有时候也去北大坑北面的树林里,捡拾地上被风摇断的干树枝,时间久了,就攒成小堆;反正这一片儿是我的领地,不会担心我的成果被别人偷走。
圈猪的时候,父亲肩上的担子就重了,有时候是满满两筐晒干的青草牛粪,有时候是满满两筐折成短节的干树枝。有时,父亲的筐里也会装满捡来的牛骨,扁担压着肩膀,一颤一颤随着步伐上下起伏。这样,我家的院子里就比较充实了,这边是牛粪堆,那边是树枝垛,靠近窗台边的是牛骨头堆,每隔十几天就有收破烂的赶着驴车来到我家,据说一车的牛骨能换好几块钱呢。
猪放场旁边的自然渠穿过县道,经过小桥汇入县道北侧的干渠,在河西汇入西辽河。
村班车站点设在小桥的东边,离我的地盘不远。班车每天一个往返,站点路边有三棵高大的杨树,上下车和接站的人们都在树下等候。
父亲有时候忘记带烟口袋,烟瘾犯了,便打发我去站点拣烟蒂。这个站点也成了我的领地,不但能捡到烟蒂、抽烟纸和火柴磷片,也有糖纸和硬纸壳,把硬纸壳带回家,剪成圆形,两边涂上蜡,这可是孩童中的神圣法宝。
九月,春时的猪羔子已经长成大猪,淘气得很,经常成帮结队逃窜到庄稼地,天黑了才肯或三或五地出来;父亲、母亲和哥哥们一个劲地向猪主人道歉,回过头来对我的过错表示绝不饶恕。我仿佛犯了弥天大错,擦抹着鼻涕,红着眼圈,饭也不肯吃,在大人的脚底下草草睡了。
有一口猪穿过树林,进入一排土房的院子,经过长距离追赶,它也有些跑不动了,在一间房子墙角等待我哗楞棒子的招呼:十步之内,见头打头,见尾打尾,它是尝过我的绝招的。
房子的门开着,哗楞棒子碰击猪嘴巴子声、落地声和猪的惨叫声在我看来稀松平常,可房子里的人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大人健步冲出来,看看正在晃头转圈的猪,回过头又看看气势汹汹的我。一群孩子也从房子里探出头来:
“放猪娃,又攒够‘法宝’了吗?”
“捡牛骨头卖的钱你妈给你买糖吃了吗?”
“黑小子,好好放猪吧,整丢一头你爸说让你当猪呢!”……
七嘴八舌后,跟着一片爽朗的欢笑声。
当天夜里,全家八口人在油灯下开会。“你两个哥哥都在上学,妹妹弟弟们还都小;生产队已经解散5年了,现在是单干,家里没有劳动力,全村人为了照顾咱们家才让咱们放猪的。你要是上学了,没有你的帮衬,你爸这身子骨肯定是放不了的,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母亲一边用纳鞋底的锥子拨动灯芯,一边好像在自言自语,也好像在跟我说话,因为那个“你”字她说得特别轻,特别模糊,我看到了她眼圈的红晕。
父亲一袋接一袋地抽烟,烟袋锅的火星子迎合着油灯的火苗子,一闪一闪的,呛人眼睛;妹妹弟弟不知道啥时候睡着了,屋里一片寂静。
我站在炕边一动不动,小黑手抠着炕沿木纹间乌黑的油渍,眼睛顺着烟雾飘向窗外……